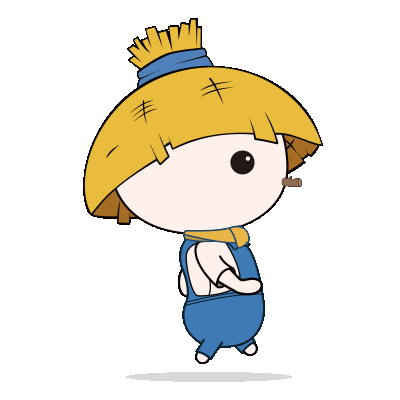罗源县
青砖高墙在毒日头下泛着白炽的金属光泽,墙根裂开的缝隙里蒸腾出硫磺般的热气。
百来个流民像晒蔫的蝗虫贴伏在墙影里,汗碱在他们后背结成灰白的盐壳,随呼吸簌簌剥落。
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在人群中炸响,有个佝偻汉子突然弓腰喷出团黑绿黏液,里面蠕动着米粒大的白蛆。
“粮仓…咳咳…定是粮仓!”独眼汉子脖颈布满流脓的疥疮,柴刀刮过墙砖时脓包爆裂,黄水顺着刀刃往下淌。
人群里爆发出干哑的嘶吼,干瘦的老头正用溃烂的手指抠挖墙缝,他手背上的红斑己蔓延成腐肉,露出森森掌骨。
竹梯撞击声惊起砖缝里的蝎子。当少年开始攀爬时,他小腿肚的烂疮正往下滴着粉红色组织液,每蹬一步都在竹竿上留下粘稠的印记。
攀到第三阶时,溃烂的脚趾突然打滑,竹刺扎进他膝盖后方鼓胀的水泡,脓血顺着竹节蜿蜒成暗黄的溪流。
围墙内的人给了当头一棒,颅骨碎裂的声响混着人群的尖叫炸开。少年身子坠落时,十几双生满癣斑的手己插进他大腿根。
有个女人边撕咬肝脏边抓挠后背,指甲带起大块带血的皮屑——她肩胛处新生的疱疹正在烈日下爆浆,黄水渗进嘴角也浑然不觉。
第二个跌落者喉咙里卡着带血的浓痰,破风箱般的呼吸声随着竹茬贯喉戛然而止。
裹着破袈裟的和尚突然剧烈抽搐,他掀开的衣襟下露出紫黑的腹部,密密麻麻的出血点像熟透的杨梅正在溃烂。
当第三具尸体被撕碎时,竹竿裂缝里渗出腥臭的黑血。墙头藤蔓上挂着的肠衣沾满绿头苍蝇。
有个少年正用溃烂的牙龈啃咬半腐的指节,他脖颈处的淋巴肿得像串发霉的葡萄。
日头偏西时,此起彼伏的咳血声在墙下回荡。独眼汉子啃咬的腿骨上粘着灰白癣皮,他每吞咽一次,喉头紫黑的淋巴结就鼓起鸽蛋大的包块。
热风卷着腐臭的布片掠过墙头,某具半腐的尸体眼眶里突然钻出蜈蚣,细脚划过曝晒过的角膜发出沙沙轻响,这些人居然拖着尸体一路走来。
青砖影里浮动着细碎的金斑,吴县尉攥着铁皮棍的手指节发白。
他看着墙外某个流民撕下自己溃烂的脸皮塞进嘴里,胃袋突然抽搐着顶到喉头——那溃皮下露出的不是血肉,而是密密麻麻蠕动的白卵。
“县尉快看!”衙役突然扯住他衣袖,枯瘦的指尖几乎掐进他肉里。
墙根阴影里躺着个抽搐的老妇,她的肚皮涨大如鼓。
忽然噗嗤一声,腥臭的血从她鼻孔钻出,在沙地上喷出了个血洼。
周一领着人在把正厅廊下的青砖一块块撬开,二十几个精壮汉子正用木桶从地窖往上吊运黑油。
这些银窖里封存的火油,历经百年反而愈发粘稠,在烈日下泛着诡异的蓝光。
他家老太爷曾一次又一次的叮嘱,不到万不得己万万不可用。
“戌时左右会刮东南风。”周一看着最后一桶火油被搬出地道说道。
“把西墙根那三十坛硫磺粉混进陈粮,等他们抢食时... ...”
“去后院那跟后墙外的流民说戌时在正门给他们发粮食。”刘县丞指挥衙役去喊话。
更漏声里,五辆独轮车吱呀呀推过中庭。车上麻袋渗出暗黄粉末,混着霉变的米香,在热浪里酿出甜腻的毒。
围墙外热闹了起来,“后墙的都过来了!”衙役过来汇报。
刘县丞点了一下头,墙头垂下十条浸油的草绳,末端系着的糜饼在暮色中泛着油光。
流民们脖颈的烂疮突然剧烈跳动,那个啃食自己指骨的少年最先扑向晃动的诱饵。
“把嘴张开,张开,”菜籽油混着桐油被一瓢一瓢地泼了下去。
当独眼汉子察觉不对时,三百斤硫磺粉正顺着他们溃烂的食道滑入胃囊。
“他们要烧死我们!”独眼汉子边喊边拉拽边上的人,“他们要烧死我们!”独眼汉子绝望的呼喊。
旁边的人愤怒地推开他的拉扯,他的话没有惊起一点波澜,在食物面前,他的话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戌时的梆子声混着东南风撞上高墙。吴县尉将火把扔进桐油沟的刹那,墙外突然亮起幽蓝的鬼火——是流民们溃烂的皮肤在燃烧。
人群轰然炸开,万千火星裹着带疫的碎肉飞溅,却在撞上桐油火墙时化作青烟。
人群里突然发出夜枭般的惨笑。衙役扒着墙头看见独眼汉子在火中舞蹈,焦黑的表皮簌簌脱落。
焦臭的浓烟持续了整整三个时辰。刘县丞和吴县尉仿佛被抽掉了灵魂般站在墙头看着下面的炼狱,久久没有言语。
月光像层发霉的纱帐罩在后院,二十几个妇孺紧贴着井台蜷缩。前院突然传来木门落闩的闷响。
“己经焚... ...”年轻媳妇的话头卡在喉咙里。晾药草的竹匾被夜风吹得咯吱作响,盖不住人群里此起彼伏的吞咽声——都在把涌到嘴边的咳嗽往肚里咽。
李寡妇的鞋底针尖戳破了手指。她借着月光瞥见怀里的婴孩后颈泛起红疹,慌忙用补鞋的破布缠住那截细嫩的脖子。
角落里周婆子的咳嗽声像钝刀刮过树皮,老人把带血的帕子团进袖口,佝偻着背往阴影深处挪了半尺。
小满忽然剧烈颤抖,陶罐里的野蕨菜根撒了一地。他娘死死捂住他的嘴,孩子脖颈上浮起的肿块隔着粗布衣料发烫。
墙角传来窸窣声,是赵娘子在悄悄褪去腕上的银镯——那镯子内侧沾着道可疑的黄渍。
吴嫂怀中的婴孩突然蹬腿大哭。十几道目光利箭般射来,她哆嗦着扯开衣襟喂奶,露出乳房上几颗暗红的斑点。哭声戛然而止,婴孩嘴角溢出的奶汁混着血丝。
周婆子剧烈哆嗦起来,袖中血帕子滑落在晒干的糙米堆里,正在纳鞋底的张嫂用针尖悄悄把帕子挑进灶灰。
卯初时分,李寡妇感觉怀中的孩子越来越烫,解开破布时发现红疹己蔓延到耳后。她突然抓起把角落里的土灰抹在孩子脸上,混着唾沫涂成青灰的死色。
晨光初现时,人们开始清点要带走的家当。吴娘子突然指着阿满惊叫:“你袖口沾的什么?”孩子腕上粘着片带血的指甲盖,不知是昨夜哪个死者挣扎时崩飞的。
人群哗啦散开,阿满娘发疯似的撕扯孩子衣袖,粗布裂帛声里飞出几根灰白的毛发。
人群的嘈杂引起了护院的注意,刚要走近,就被喝住。
“莫要走近!去叫县丞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