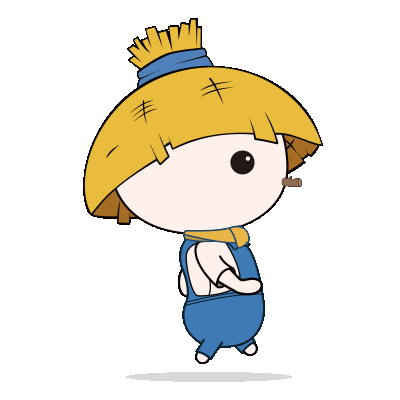浓雾裹着山尖时,阿禾用草绳把弟弟的裤脚扎了三道。八岁的阿谷背着草绳裹着的小铁锅,拿着一把豁了好几个口的破菜刀。腰上别着两个大竹筒,里面早就没有一滴水了。
阿谷盯着村口老榕树上飘摇的破布条,那是里正家撤离时系的红布条,此刻己褪成了惨白。
逃荒的队伍三天前就离开了,留下西五户走不动的人家,昨夜村西头王寡妇家的炊烟再没升起过。
她家己没有余粮,就是踏上逃荒的路也难走到几百里外的汀州府。官道上流民传来的消息说,汀州府城门早落了千斤闸,城郊的观音土都被掘尽了。
而且她的亲人都己陆续离世,只剩她和弟弟相依为命。这里己经旱了两年,青河村十八口井早就陆续见了底,春天己过还没下过一滴雨,连祠堂前的百年老樟都枯成了劈柴。
听说有些地方旱了更久,还有蝗灾,赤地千里,人吃人,人间炼狱!这时候跟着族人离开,她怕最后两人都成为别人的盘中餐。
山道上的碎石硌着草鞋,阿禾望着雾中若隐若现的苍黑色山影。心想她和弟弟的活路只有这终年云雾缭绕的九重山。虽未下雨,但山上的大树依然苍翠,村里人不敢深入这九重山,但却把外围几座山踏遍了,都没找到水源,近日连石壁缝隙都己没有了水。
“阿姐,陈阿公说山里有吃人的瘴鬼。"阿谷的肚子发出鸣响,像只离巢的雏雀。阿禾后背别了一把柴刀,一只手攥紧他嶙峋的手腕;一只手扯了扯身上的青布包袱,里面只有最后半块掺了麸皮的蕨菜根饼,和一张用了两年的油布,几件衣服。
阿谷忽然拽她衣袖。雾霭深处传来细碎的响动,似是石砾滚落的声音。阿禾摸出别在腰后的柴刀,刀刃上还沾着之前宰杀那唯一一只老母鸡时的褐血。山风卷起她散乱的发丝,露出颈后新起的疖子——这是连吃七日蕨根的后症。
“跟着我。”她把弟弟往身后拢了拢。枯黄的蕨草从石缝里钻出来,像无数干瘪的手指。转过鹰嘴岩,再走一炷香的时间就来到了九重山腹地,这里人迹罕至,危机重重。
阿禾踢到个硬物,低头竟是半截陶罐,内壁结着青苔。她的指尖突然颤抖,罐底残存的水渍在夕照下泛着油光。
狼嚎就是在这时刺破雾霭的。阿谷的惊叫卡在喉咙里,变成短促的抽气。阿禾反手将人推进岩缝,柴刀,铁锅撞上山石迸出火星。暗绿色的兽瞳在十步开外闪烁,她闻到了腐肉混着湿毛的腥气。
二人顺着岩壁越挤越深,岩壁的湿气渗进她的胸膛,她的手摸到腰间束着的火折子——逃荒前夜,她在灶膛灰里埋了整宿才存下这点火种。
狼爪刨地的声响越来越近。阿禾咬破舌尖,在血腥味中扯出火折子。当第一簇火苗蹿起时,她看见岩洞深处隐约有钟乳石的反光,她听到了滴答滴答的水声正从黑暗深处传来。
阿谷拉了拉她二人以更快的速度挤过山缝,刚站稳,阿禾把火折子往阿谷方向一塞“拿好”。说着举起了柴刀,借着火折子的微光,狠狠的劈了下去。
柴刀砍进狼颈的钝响混着骨裂声,阿禾的虎口被震得发麻。第一匹狼的血喷在岩壁上时,第二匹灰狼正卡在岩缝里龇牙——这处天然石闸最窄处不过两尺,上大下小成了绝佳的屠狼口。
“砸眼睛!”阿禾嘶喊着把石块塞进阿谷手里。八岁的孩子红着眼将石块抡出个半弧,正中灰狼左眼。畜生吃痛缩头的刹那,阿禾的柴刀从它张开的血口捅进去,刀尖搅动时碰到个硬物,竟是半截嵌在狼牙间的银簪——这恐怕是月前失踪的采药女春桃的遗物。
狼群在五步外刨地,火折子的光晕里浮动着六点幽绿。阿禾攥紧簪子退向洞窟深处,忽然瞥见钟乳石柱上缠着条五彩斑斓的长影。那蛇信吞吐的瞬间,她猛地将弟弟按倒在地。
“莫动!”簪尖破空的声音比话语更快。淬过狼血的银簪贯穿蛇头,将一尺来长的毒蛇钉死在石壁上。蛇尾拍打处,几滴毒液正落在他俩先前站立的位置,滋滋腐蚀着青苔。
阿谷瘫坐在湿滑的地面,后知后觉地发抖。阿禾先将蛇头用柴刀砍下,蛇身顺着柴刀紧紧绞着她的手腕,鳞片刮出数道血痕。她借着火光细看,这蛇头呈三角,背纹如铜钱套叠,这肯定是条毒蛇。
洞外狼嚎忽转凄厉,残留的狼群竟扯走了同类的尸体,在崖缝外开始抢夺撕咬同类的尸体。阿禾捂住弟弟的眼睛,自己却死死盯着这幕——这些本该油光水滑的秋狼瘦得肋骨分明,啃食同类时连皮毛都囫囵吞下。
火苗突然爆出个灯花,照亮了他们身后的洞窟。洞穴很深,钟乳石上滴下的水,形成了一个片片水田的错觉。
阳光也是这时穿过崖缝,光带里浮动着金色尘粒也微微照亮了这个山洞,狼群退去。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姐弟俩借着微弱的光,给肚子灌了个水饱。折了几根树枝,找来枯枝落叶在洞内点燃一堆篝火,篝火照亮了整个山洞。
“阿姐,快看!”崖壁上竟悬着片歪斜的木栈道,腐坏的绳结上还系着半枚元宝铜钱。
“上面还有个山洞,我们去砍根长树杆,斜放着应该能爬上去。”阿禾绕着山洞观察过后说道。
二人在崖壁外找了棵不大不小的杉树,阿禾教弟弟用火折子燎烤树干底部,这是村里老木匠伐巨木时用的巧劲。待树干将倒时,她拉住阿谷的肩膀:“往左后方跳!”轰然倒下的杉树哗哗一阵巨响,惊起一堆尘土。
阿禾用柴刀把枝大部分桠去掉,留下几节较粗的枝干,在主干每间隔两尺的地方用柴刀砍几个坎,半抬半拉给扯进了山洞。等把树杆固定,二人轻轻松松爬上了这个隐秘的山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