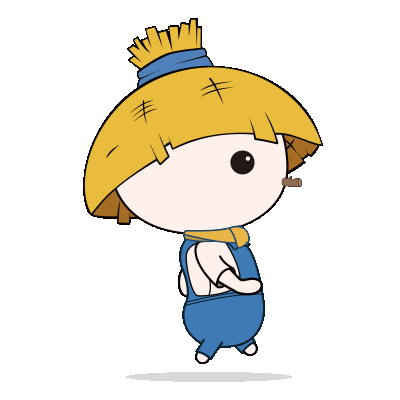随着敲击冰面的“铛铛声”消失后,一个喘着粗气的声音在远处响起。
“旺哥,洞凿开了。”
江旺手中烟头顶端的火光越来越暗,随着他的手臂轻轻一挥,暗沉的红点在空中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最后落在了我的脚边。
江旺叹了口气,缓缓起身,惴惴不安中我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一刻,在昏黄车灯的照射下,他的脸上不再有之前复杂的神情,恢复了往日的嗜血与癫狂。
没有任何犹豫和迟疑,他干脆的向着前方黑暗中走去,寒风中飘来他毫无感情的声音:“细狗,你们送他上路吧。”
我M,他们竟然真的要杀了我,我彻底慌了,死死赖在地上不肯起来。
三个人走到我的边上,就像处理一只待宰羔羊般将我五花大绑了起来,全然不顾我撕心裂肺的呐喊。
我就这样被他们在冰面上向前拖行着,耳边除了他们粗重的喘息声,就只剩下自已那近乎孩童般的哭喊声在山谷中回荡。
此时天空的月亮正值当头,也是它最亮的时候,暗沉了一晚上,仿若就是为了此刻替我送行。
“MD,把他塞下去。”
随着他们七手八脚的动作,我的腿已经被塞进了冰窟窿里,一瞬间刺骨的寒意自腿部袭来,冰冷潮湿的裤管黏着小腿,如同有无数只死人的手在抓我,求生本能的驱使下,我拼了命的拍打撕咬着抓着我的手,
“M,还敢咬我。”
伴随着咒骂声,两记凶猛的重拳直接击打在我的面门之上,一阵眩晕感后我终于失去了反抗的力气。
随后湿冷自小腿、大腿、腰部,一路便来到了我的胸口。
看着黑暗中江旺那若隐若现的身影,我几乎祈求般喊道:“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我真的不想死啊!”
哭喊声中,我恍惚看到自已眼前站了两个自已,一个穿着一身黑衣,一个则穿着一身白衣。
白衣摇了摇头,满脸悲痛之色,黑衣嘴角挂着瘆人的笑意,一副看动物的模样。
两个人交错着同时开口:“陈默,活下去,还有一堆重要的人等着你回去呢!你也就这德行,不是自诩高傲,怎么面对死亡这副德性了?一会可别再尿裤子了。”
那两个声音我听得真切,的确是我自已的声音,但却又那样的陌生。
我不禁在心里问自已:这是我的声音吗?为什么时而熟悉又这般陌生。
也许这就是人们传说中的阴差吧?所以我应该是看到了自已的死亡,刚刚那交错回荡的声音当然是我发出来的,陌生感是因为它源自于死亡。
当冰寒刺骨的湖水没过我的脖子时,我听到了远处江旺焦急的声音。
“等一下,先拉他上来。”
随着这声犹如皇帝大赦般的指令,我被从冰窟里拉了上来。
浑身湿透的我蜷缩在地上,死死的抱着自已的双腿,牙齿上下不规则的碰撞着,微弱的灯光中,我看到江旺好像在打电话。
慢慢的我终于止住了抽泣,大脑也开始思考着可能的一切。
江旺在跟谁打电话?
刚刚只需要两分钟我就死了,他为什么拉我上来?
拉我上来是不杀我了吗?还是迟一点再杀我?
还是说他有其他打算,从我身上再榨取点价值?
就在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时,江旺已经打完电话,缓缓向我走来,他将一件厚重的棉大衣披在我的身上。
“细狗,去生个火堆,别把他冻死了。”江旺将我从冰面上搀扶起来,对着边上的人吩咐道。
“哥,啥意思,不整死他了?”那个叫细狗的语气有些不悦,“这地方可不安全,要是警察找到这,咱们就全完了。”
“别TM废话,赶紧去,一会先生要过来。”
江旺说完先生两个字,后者脸色明显一沉,没有过多的犹豫,便招呼边上的人去捡柴火了。
江旺先将我领进了车内,他的脸色很不好看,也没有想要和我说话的意思,只是拿出两支烟,塞了一支进我的嘴里,并帮我点燃。
我也并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安静的坐着,紧紧的裹着身上大衣,大口大口的抽着烟。
我知道多说无益,面对江旺这样的亡命徒,我说与不说,只要他想杀我,我就一定会死,不然则反之。
惨白的月光照射在江旺的脸上,我几乎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挣扎和不安,那首打油诗忽然就跳进了我的脑中。
先生?难道是打油诗第一位提及的先生?一定是了,普通人不会叫这样的名字,普通人不会对精神病江旺造成这等威压。
我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连连猛吸了几口烟,直到灼烧感从指尖传来,我才扔掉了早已燃到尽头的烟蒂。
就在这时,江旺手机的铃声在空旷的野外响了起来。
“闻老师,您到哪了?对对对,你过了大桥掉头,从桥下过来,顺着小路十分钟就能到,好好好,我等您。”
江旺挂了电话,冷冷的看了我一眼,仿佛要为刚刚接电话时卑微的语气找回一丝颜面。
见我没有反应,我看了看远处,随后指了指早已燃烧起来的火堆。
“走吧,过去烤烤火吧,就你这一身湿不烤干了,恐怕撑不到十分钟。”
于是我像个落水的孩童跟在他的身后向火堆走去。
脱掉大衣,站在火堆前贪婪地享受着火焰带给我的温暖,几分钟后,哆嗦终于止住了,被烤的有些发烫的双手,竟让我生出了一丝怪异的。
大约又过了几分钟,远处射来上下跳动的灯光,与我们眼前昏黄的灯光不同,那是只有氙气大灯才能发出的通透白光。
随着光柱跳动的幅度越来越小,最后变为直线,一辆奥迪Q7停在了我们的面前。
一时间现在的气氛变得极为奇怪,我隐隐约约仿佛闻到了紧张的味道,但同时又有种野兽身上才会有的嗜血的气味。
江旺不自觉的摸了摸自已后腰的手枪,仿佛要确定它还在那里,而他的几名手下,也仿佛石化一般,站在原地大气不敢喘。
就在这时,驾驶室的门被打开了,一个穿着米白色大衣的男人从车上下来了。
男人约摸四十岁上下的样子,板寸头、金丝眼镜、白皙且文静,他笑了笑,挥手示意后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