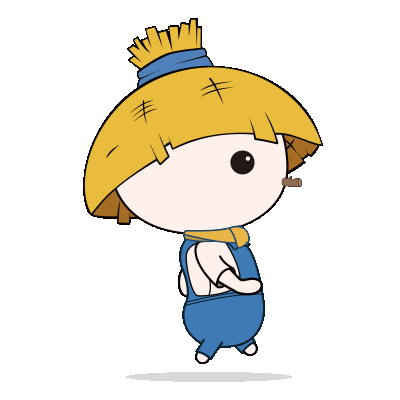白大太太心领神会,拍拍她的手,笑道,“咱们就是话赶话的说到这儿,哪能当真呢。你父亲聪明一世,也没人敢在他面前弄鬼。”
凭许弦声对公婆两人关系的了解,白大太太后一句绝对是嘲讽。
又坐了会儿,便识趣地告辞。
她一走,白大太太便沉下脸,让人去找另一名心腹方管事。
方管事和孙管事一样,都是她一手提拔的。
不多时方管事来到,白大太太吩咐道,“五姨太从江南带来了两个人,老妈子金妈、小丫头石榴,只要她们一出白家,就给我盯紧了。”
又对陈妈道,“她们在白家的时候,你派人留意着。”
等方管事领命退下,陈妈迟疑道,“大太太,您信三少奶奶?”
白大太太一笑,“查一查,也不费什么事儿。”
江南她都能派人去,何况只是就近盯着两个内宅妇孺。
慧莹这神来一笔,让她想起一件事,五姨太的奸夫,可能不仅仅是奸夫,还是同伙。
如果真有,定然也跟着来了闻桐城,通过金妈或石榴与五姨太联系,只要盯紧她们,就能摸到蛛丝马迹。
哪怕慧莹猜错了,也没什么损失,还有江南那条线。
陈妈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三少奶奶老实巴交的,怎么能想到这上头?”
什么提起江南就想到仙人跳,她不信。
她也听说过仙人跳,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白大太太叹道,“这孩子有心了,她是想帮忙。”
而且颇为通透,并不囿于一般的家宅内斗,直接从根上入手。
五姨太那做派,除了大老爷,谁都看得出来不像良家。
所以慧莹就提醒她,五姨太的来历有问题,不要在细枝末节上纠缠,要釜底抽薪。
仙人跳,估计只是个歪打正着的说辞。
大老爷可以纳扬州瘦马,却不能纳个女骗子。
说到帮忙,陈妈想起另一个人,愤愤道,“五小姐这游学,来得可真巧。”
早不去晚不去,偏这个时候去。
白大太太默然数息,淡淡道,“趋吉避凶,两不相帮,明哲保身,也是人之常情。”
游学三个月,三个月后,白家大房谁占上风想必也明朗了。
到时回来,就不用在父母之间为难,谁都不得罪。
这心思,啧啧。
陈妈气道,“我说句僭越的话,您精心教养她十多年,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竟然比不上常年不在家的大老爷。”
小白眼狼。
白大太太并不生气,“那毕竟是她的亲生父亲,我却不是她生母。”
慧莹的心性,从小就有些凉薄,她早就发现了。
因而此时并不觉得有多失望。
陈妈替主子不值,“唉,不是自已生的,就是养不熟......”
说到这儿忽然想起,亲生的也不一定养得熟,例如八少爷,连忙收住话。
白大太太没联想起小儿子,豁达地道,“跟个小孩子计较什么。”
陈妈:“三少奶奶也没比五小姐大多少,只来了几个月,就知道替婆母分忧。”
白大太太微笑,“这人呐,性情都是天生的。”
有人天生重情重义,有人天生自私自利。
得了别人的恩惠,有些人恨不得涌泉相报,有些人却觉得理所当然,还嫌太少,这都是天性。
——
今日天气甚好,许弦声便没急着回绿萝院,而是带着春杏,绕到池塘边看了会儿鱼。
她刚学女红的时候,祖母就教过她看鱼养眼。
长时间盯着针线,眼睛会酸涩干枯,让视线跟着鱼在水中游动,就能有所缓解,还能越来越明亮有神。
所以她常来池塘边。
白家这池塘不算大,边上栽了几株荷花,此时开得正好,春杏折了两枝,说要带回去插瓶。
许弦声并未阻止。
园里的花儿朵儿,白大太太也常令花匠摘了送到各房,只要不全部搂干净,便无人在意。
“三嫂!”
白承玮忽然从一旁走来。
许弦声点点头,“八弟也来看花?”
白承玮面容憔悴,“三嫂肯定也觉得,我不识好歹,不分对错,糊涂透顶,没良心,帮着父亲和五姨太欺负母亲!”
许弦声:“......我没这么说过。”
是你自已说的。
白承玮声音沙哑,“可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我是有苦衷的!”
三嫂是个善良的人,他不想她误会自已。
说这话时,他身子微微颤抖,双手紧紧攥住,像是内心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许弦声不禁问道,“什么苦衷?”
白承玮用力摇头,咬牙道,“我不能说,不能说!”
许弦声不知他玩的哪一出,“八弟,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开呢?你若不愿跟我说,那就跟母亲说吧!”
白承玮更痛苦了,“她心知肚明!明明是她有错在先,对不住父亲!”
许弦声:“......究竟是什么事?”
她实在想不出,白大太太会有哪一点对不住白大老爷。
白大老爷对不住白大太太的事迹,倒是一抓一大把。
以她看来,白大老爷根本配不上白大太太。
“我不能说!”
白承玮擦一把眼泪,悲伤地看许弦声一眼,低头跑开。
春杏:“......八少爷真是,莫名其妙。”
许弦声也觉得莫名其妙,想半天想不明白,抱着荷花回绿萝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