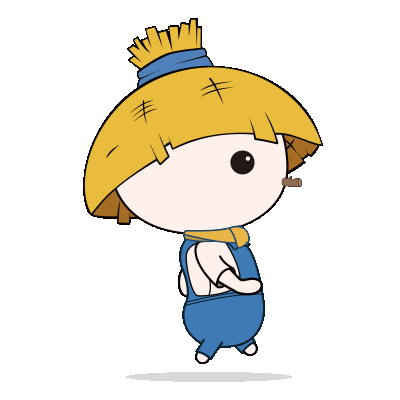宴席散时,天已黑尽。
白大太太嘱咐白承璟与媳妇一道回绿萝院,白承璟笑着应下。
但一离开白大太太视线,就快走几步,没一会儿便看不见身影,也不知去哪儿了。
春杏打着灯笼引路,嘴里小声嘟囔,“三少爷也真是的!”
许弦声:“三少爷这样,你第一天知道?”
春杏不说了。
次日起来,许弦声翻检自已的嫁妆,发现东西不少,现钱却只有两百大洋,其中的九十,还是她嫁过来这三个月,从白家得的月例。
可她需要至少一千大洋。
八百的空缺,怎么补呢?
许弦声盯上了柜子里那些布料。
都是好料子,她一个人,根本用不了这么多。
叫来春杏,吩咐道,“我的雪花膏快用完了,你下午去街上买两盒,给你一盒。顺便打听打听,哪儿有收布料的,价钱多少。”
听说能得一盒雪花膏,春杏很高兴,又不解为何要打听布料价钱。
“三少奶奶,打听那做什么?”
许弦声不想告诉她实情,“叫你打听就打听,别多问。”
春杏:“......是。”
感觉三少奶奶变得很有主见。
主仆俩正说着,院外有人敲门,王妈去洗衣裳了,不在院中。
春杏一边问“谁呀”,一边飞跑着去开。
许弦声也走到门口张望,下一秒,她愣住了。
来者容长脸,瘦高个儿,竟是霍珝的副官,姓李。
她对此人印象深刻。
因为,前世错认她为下人的,正是他。
李副官很守礼,并不进屋,只在院里讲话。
将手里的礼盒交给春杏,对许弦声笑道,“三少奶奶,鄙人姓李,忝为霍少帅副官。少帅昨日认错了人,越想越过意不去,觉得对不住您。特意命我送上薄礼,还望三少奶奶谅解。”
许弦声从来不知道,霍珝竟是这么客气的人。
她也没遇上过这种事情,不知如何处理,愣了会儿才道,“不敢当,请转告霍少帅,我并无芥蒂,礼物也请带回去。”
春杏也上前一步,要将礼盒还给李副官。
李副官不收,笑道,“送出来的礼物,哪有收回去的理儿。三少奶奶若不收下,少帅定然怪我不会办事,您就别为难我了!”
他把话说到这份儿上,许弦声也只得道,“既如此,我就愧领了,多谢霍少帅,也多谢您。”
李副官却不告辞,神情踌躇了下,摸了摸鼻子,道,“有句话,霍少帅令我转告三少奶奶。”
许弦声纳闷,霍珝跟她有什么话好说?
“您请讲。”
李副官目光下垂,不看她的脸,“少帅说,他会管教三少爷,让其收心,也请您清静自守,宜家宜室。”
许弦声的脸一下子红了,气的。
对于她这种听着女德长大的人来说,有人告诫她清静自守,那几乎等同于指着她的额头,骂她轻浮浪荡。
可霍珝凭什么?
他凭什么侮辱她?
就因为看了他几眼?!
天地良心,看他的又不止她一个,谁不对他好奇,谁不看他?
而且这样的时代,男女搂着跳舞,把臂同游都不算大问题,凭什么因为看他的那几眼,就认定她不够清静自守?
就算她真有错,也轮不到他来教训!
他并不是她的长辈!
李副官也觉得,少帅管得有点宽,姑母家的表弟妹,轮不到他这当表哥的来管教。
因此话一传完,转身就走。
不敢看许弦声脸色。
“站住!”
许弦声深吸口气,“我也有句话,请转告你家少帅。”
李副官尴尬地道,“您说。”
许弦声:“霍少帅真是能者多劳,老太爷、大老爷、大太太管教不了的三少爷,霍少帅竟能管教下来,厉害!我在此先谢过,也等着三少爷在霍少帅的管教之下,有所长进。”
李副官暗想你这可不是一句,是很多句。
回到客院,一一转述。
霍珝沉默半晌,问道,“她真这么说?”
李副官笑道,“我哪敢骗您?真这么说了!这位三少奶奶可不简单。”
霍珝冷哼一声,“牙尖嘴利!”
也不知是在说许弦声,还是在说李副官。
一挥手,李副官唯唯退下。
绿萝院里,许弦声兀自生气。
又见春杏还捧着礼盒站在一旁,眉头一皱,道,“你送去客院。跟霍少帅说礼太重,我不敢收。”
春杏:“......您还没看呢,怎么就知道礼重。”
许弦声瞪着她,不说话。
春杏不敢再犟嘴,苦着脸道,“三少奶奶,我不敢。”
她不傻,知道将别人送的礼物还回去相当于打脸。
那可是霍少帅,她怎么敢?
在她眼里,霍少帅跟戏里的青天大老爷似的,又威严又庄重,叫人无法违逆。
而且,他手下那些扈从都有枪。
她怕自已直着进去,躺着出来。
许弦声怒道,“胆子这么小,怎么当人丫头!”
春杏赔笑道,“以前我娘就说过,我这胆子跟老鼠似的。三少奶奶,要不您受累,咱俩一起去?”
许弦声不语。
想到要直面霍珝,心里也有些发怵。
沉默半晌,打消了将礼盒送回去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