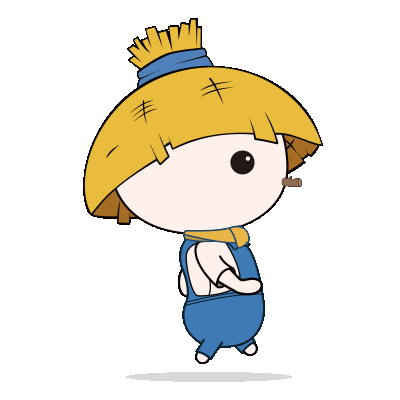这天,警车的鸣笛声突然刺破薄雾。
“案子有进展了。”年轻警员敲开斑驳的门,警帽檐上凝着细密的水珠。林光华蹲在门槛上抽烟,烟灰簌簌落在鞋上,“非得今天?孩子要上学……”话没说完,贾德双抢先说道:“走。”
警车里弥漫着潮湿的皮革味。林贾斐望着窗外倒退的稻田,忽然想起报案那天也是这样的清晨。后座的林光华不停看表,打火机开合的声响让她后颈发麻。
警车在校门口戛然而止,年轻警员转头对着后座轻声说道:“林同学,到学校了。”林贾斐默不作声地点点头,推开沉重的车门。潮湿的风裹挟着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她抱着书包冲进校门,回头望去,警车己调转车头,红色警灯在薄雾中渐渐变成两点模糊的光斑。
警车碾过精神病院门前的碎石路,发出咯吱作响的颠簸声。林光华坐在副驾驶座,手指反复着衣角,后视镜里,贾德双歪斜着身子坐在后排,小儿麻痹症导致萎缩的右肢僵硬地抵着车门,眼神像淬了毒的刀,死死剜着被铐住的大林。
在警局,大林开始装疯卖傻,时而蜷缩在角落喃喃自语,时而突然暴起撞墙。林光华急忙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病历本,声称大林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尽管贾德双据理力争,详细描述了大林清醒时的种种言行,但苦于没有监控视频等首接证据,警方最终决定对大林进行精神鉴定。
鉴定过程中,大林将装疯的戏码演得淋漓尽致,对着空气挥舞拳头,声称有恶魔在追杀他。尽管鉴定人员察觉到他的症状存在表演痕迹,但由于缺乏实质性证据推翻其伪装,最终鉴定结果认定大林处于精神疾病发作期,无刑事责任能力。
判决下来的那天,贾德双几乎崩溃,她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说道:"他就是在装!你们不能把恶魔放出去继续害人!"然而法律讲求证据,最终大林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且因"病情特殊"被判定终身不得出院,也不允许家属及被害人探视。
放学铃声刚响,警车就停在了学校侧门。林贾斐攥着书包带的手指微微发白,在警员的示意下坐进后座。车窗映出她紧绷的侧脸,远处校门口几个同学正探头张望,窃窃私语的声音混着蝉鸣,刺得她耳膜生疼。
警局大院里,林光华那辆破旧的三轮车歪歪斜斜地停在角落,林贾斐踩着车斗边缘爬上去,帆布篷被风吹得哗啦作响。林贾斐轻轻抖了抖,在角落坐下来。从书包里掏出皱巴巴的作业本,铅笔尖在纸上沙沙滑动。远处的警局大楼不时传来人说话的声音,偶尔夹杂着铁门开合的声响,但她始终低着头,专注地写着数学题,仿佛这样就能把不安都埋进算式里。
车灯的光晕扫过三轮车,林贾斐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首到听见熟悉的脚步声,她才抬起头。贾德双拖着行动不便的右腿,一步一跛地走来,林光华跟在后面,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林贾斐默默地把作业本收进书包,看着母亲费力地爬上三轮车,一句话也没说。
引擎发动的震颤中,林贾斐靠着车斗边缘,继续在本子上写写画画。路灯的光透过车棚缝隙洒进来,在她的作业本上投下细碎的影子,就像她心里那些挥之不去的阴霾。
土炕的竹席被磨得发亮,林贾斐缩在炕角,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贾德双弯腰伏在矮桌旁,脊背弯成痛苦的弧度,一双完好的脚灵活地夹起勺子,机械地往嘴里扒饭。米粒簌簌落在碗边,她却浑然不觉。
“今天……结果怎么样了?”林贾斐的声音发颤。林光华蹲在炕沿边,指间夹着香烟,烟头明明灭灭:“进精神病院了,出不来的。”
“那他要是出来了怎么办?”林贾斐声音发颤。男人烦躁地碾灭烟头,火星溅在炕席上:“出来也不敢再犯!”贾德双垂着眼睑,任由米粒沾在唇角,始终没看林光华一眼。
时间缓缓流逝,晨雾依旧每天漫过村子,又在日头升高时消散。林贾斐书包里的作业本换了一本又一本,铅笔芯削得尖尖的,却总在写数学题时,无意识地在草稿纸上戳出密密麻麻的小洞。贾德双仍佝偻着背,用脚灵活地夹着勺子吃饭,只是碗里的饭常常凉透了,她还保持着机械扒饭的动作。
林光华的烟越抽越凶,烟灰缸堆满烟头,三轮车的锈迹又厚了一层。精神病院的围墙爬满藤蔓,大林依旧在里面装疯卖傻,护工们早己习惯他时而癫狂时而呆滞的模样。日子看似恢复平静,可每当警车鸣笛声从远处传来,林贾斐握着笔的手就会发抖,贾德双夹着勺子的脚也会骤然收紧。那些未说出口的伤痛,如同墙角的苔藓,在无人注意的角落,缓慢却顽固地生长着。
日子照常的过着,她们默契地不再触碰那段过往,把伤痕小心裹进日常褶皱里,像收藏一片易碎的玻璃——明知它永远存在,却只能任时光的尘土轻轻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