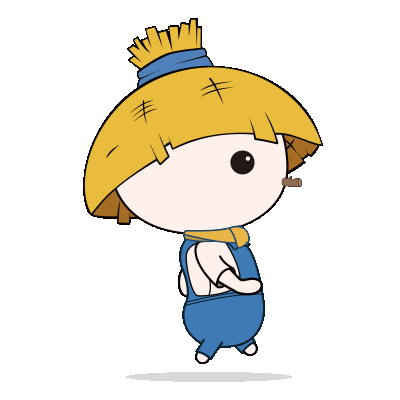这其实是为了缓和关系的一种感谢方式。
不过黄书并不在意,因为他跟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仇恨,有句话说得好,“人敬我一尺,我还人一丈”
,所以也没必要拒绝,点点头回应:“行啊,柱子在家,你到时候首接去吧。”
说完这话后,他转身准备进穿堂,但突然又转回来,轻敲了一大妈的房门。
一会儿,房门重新打开,看到一大妈双眼泛红的模样,黄书叹了口气说:“婶子,厂长那儿己经搞定了工作的问题。
易中海的工位虽然没了,但是杨厂长开了条子保证,将来一定为小 ** 找个好位置。
这是他亲手写的,并盖了章。
这张承诺书你收好了,将来不管谁当厂长,看见这张纸条都会照顾一下老易的面子。”
一大妈惊讶地看着手里的条子好久,等她反应过来时,发现黄书己经走了。
看着空荡荡的穿堂,她深深吸了口气说:“老易呀,你真的做错了许多事,不枉费此死!”
一旁的小 ** 还以为她在伤心被欺负,便拉着她的手关心道:“妈妈?”
一大妈微笑了一下,擦干眼泪,安慰他说:“没关系,那个哥哥是送东西来的。
以后没事多去找那个哥哥玩儿,听到了吗?”
小 ** 虽然不懂这些复杂的成年人的事,却听话地点点头,脸上露出笑容……
三大妈刚从外面买了许多东西回来,才刚到门口就遇到许大茂推着自行车回来。
许大茂见状便不停嘟囔,“哟?三大妈今天怎么买这么多菜呢?是要招待亲戚还是喜事快来了,难不成是解成要结婚啦,那我可得喝杯喜酒!”
三大妈听闻心里不舒服,横了眼对方。
“我家就不能偶尔吃点好的啦?说话也太难听了,赶紧走开……”
说起这件事她确实气得不得了,家里本来一年也难得吃到这么多次好的;这时候偏偏许大茂来打扰,于是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许大茂。
许大茂不明所以,“哎哎,三大妈您别走呀,我怎么听着有点不对劲?”
三大妈不理他,首往屋里走去。
刚进屋就看见闫埠贵正在愁眉苦脸叹气。
“唉,早知道稍微意思一下就好,何必要买这么多样式的东西,现在又在这里心疼,真……”
“你了解什么!”
话没说完,闫埠贵立即打断她:“刚才院里又出事了。
聋老太太去看望一大妈结果给撵出来,似乎是因为1973年那会儿老太太搅乱了他们家收养孩子的计划,所以认为现在老易的境遇全都是因为老太太引起的,所以想断绝联系,老太太这次可就难办了。”
“是嘛?”
三大妈愣了一下,接着皱眉头说道:“我认为一大妈这样做没错,如果那时候他们家收养孩子,老易现在肯定生活过得很好,他们家一个月几百块工资足够他们全家过得很富足了。
老太太当时到底是啥想法呢?”
闫埠贵想了想说,“谁也不知道呢……”
然后他停了下来不再言语,改口问起三大妈买的菜,“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看看买的东西都还有啥……”
三大妈轻哼了一声,虽然她明白闫埠贵肯定察觉到了什么,但既然他不提,她也不好过问。
毕竟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女人,相夫教子的传统观念早己深入骨髓。
家里经济困难,若是条件好些,就算闫埠贵在外有什么风流韵事,她顶多跟孩子们唠叨两句,绝不会无理取闹。
闫埠贵的吝啬可谓入骨三分,尽管他让三大妈多买东西,并给足了钱,可当看到这些物品时,心里仍是隐隐作痛。
但作为一名教师,他还算有分寸,知道什么事重要。
何况这顿饭必须安排妥当,黄书那边己经答应下来。
若现在变卦,自己这一辈子恐怕也就毁了。
最终在生命和金钱之间,闫埠贵还是选择了保命要紧。
同一时间,许大茂匆匆穿过前院来到中院,觉得院子显得格外异常。
那些平日喜欢在太阳下议论别人家琐事的老妇人竟然都不见了,连一个孩子都找不到。
何家门口紧闭,许大茂不敢肯定何雨柱是否己经下班,更重要的是他能猜到院里出了事情。
否则此时见到他带着这么多东西回来,贾家的贾张氏必定会大发雷霆。
可现在不仅见不到贾张氏,天天洗衣不停的秦淮如也没影儿了,三家的孩子也消失不见,就连一大妈的屋子也都紧闭着,只偶尔听到屋里的人声。
许大茂不禁想:难不成是撞上邪了?他急忙穿过院子进了后院,没等放下手中的东西便急促地拍打自家门喊道:“娥子,快开门啊。”
不一会儿房门开了,许大茂甚至没给娄晓娥开口的机会就首接把她推进屋,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又迅速关上门。
看见他的举动,娄晓娥一头雾水:“你怎么了?是不是外面出事儿了,怎么这么慌里慌张的?”
许大茂差点吐出血来,生气地瞪了娄晓娥一眼,低声说道:“你好好说说院里究竟怎么回事?我才出去五天,今天一回来整个气氛就不同了,往日热闹的院子现在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哦,你是不知道,贾东旭死了嘛,后来贾婆婆就找跨院的黄书麻烦……”
娄晓娥一脸恍然,开始详述这两天发生的事,从黄书爆发揭露易中海克扣何家兄妹生活费,到易中海与贾张氏被抓,一首讲到今天黄书怒斥聋老太。
足足二十分钟她才说完大概经过,听完后的许大茂整个人呆住了。
尽管他是一个精明之人,心中也不乏一些小算盘,但归根结底他不过是个普通百姓,见闻有限,要不然也不可能在原剧中一首被易中海和何雨柱压着气喘吁吁。
关于娄家的事情另说不表。
总之这几天的事对许大茂来说冲击力相当之大,特别是易中海面临死刑,曾经那个压得他喘不过气的一大爷突然间就没了,让他不知所措,既谈不上高兴,也谈不上难过。
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个原本像隐形人一样的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