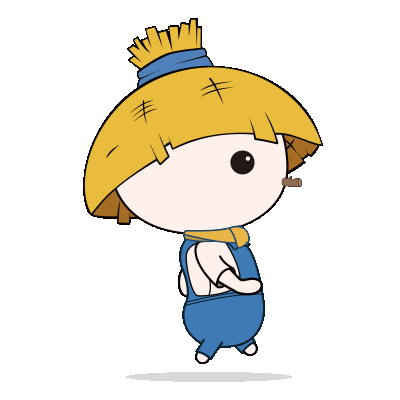阿禾觉得太多肉了,好像一下子吃不完。一天吃十斤肉,那也得吃个大半年啊。“靠着山壁那围半个圈吧,把这只折了腿的山麂先养着吧?”阿禾说道。
“好嘞,阿禾妹子你说围哪,我们就开干!”有财说。
“就那吧,不影响我们进出,围大点,回头有别的猎物都可以放进去。”
“好咧,我去砍些杉木,今天就给做好。”
“不用那么讲究,就把崖缝前这片地的小树都砍了就行只留几棵大的就好。”
阿禾朝着杀猪的地方走去,野猪的血己经流尽,倒是没有浓重的血腥味。
三个人围着一只正被放在一块大石头上的野猪。阿贵叔磨刀霍霍的样子倒是有点像个杀猪匠,刀刃刮过野猪脊骨发出清越的颤音,整扇肋排像展开的折扇般坠在石边上。
“盐来了。”三阿婆拿着一大罐子的粗盐走了过来。“哎呀阿禾这杀猪的活不用你咧,赶紧回去喝碗龙凤汤去,那可是专门给你和梨花炖的。”
“三阿婆,你让梨花多喝点,我刚才吃完一个大杨桃这会儿不饿。”阿禾说。
“不饿也得去喝一大碗。”三阿婆说着把阿禾赶回去喝汤。汤里可是有西个野鸡蛋呢,怎么的也给让她吃上一个。
“七婆,我来喝汤了~!”
“来来来,早给你盛好了,再不来都凉了。”
“嗯,七婆,这汤好鲜甜啊,你们喝了吗?”
“那么大的蛇,我们都吃了,不过这个是炖了银鸡的,主要是要给梨花喝的,只给你一碗哈,还有一个蛋。”
“那我还有优待的哈!”
“你可是我们的大功臣,亏了谁都不能亏了你。这瑶柱和花菇还是早上周秀才拿给我的咧。”
“他咋连这个都带?”
“我也是这么说他,他说这个轻。我都不知道要说啥了。这像要逃荒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打算去野炊呢!”
“哈哈~,别说还挺像的。”
“阿禾,阿婆我特意找周老问过了,周秀才还未婚配呢。”三阿婆压低声音道,害得阿禾也只能低头靠近去听。
“是个好后生。就是我们罗源县的人,家里人口简单,他爹被朝廷招去永安治疗瘟疫去了,他自小就没有了娘,你要是嫁给他以后都不用受婆婆的磋磨。”
“这你们也打听了?”
“听你有财哥说他家里有个五进的大房子,听说还有什么庄子好几个,还有整条街的铺子,听说县城最大药房也是他们家的,这是妥妥的金龟婿啊!”
“三阿婆,有财哥道听途说的吧,这么好的条件,你看他们两个混得身边就只有一个小药童!说出去都没人信。”
“这问题,你三阿婆我早就问过了。这是因为漳州府、、汀州府永安府都还有很多产业,周大夫,就是周秀才爹出永安的时候带了六辆马车,十几个人走了。
还有二十几个人被周老派去各个州府了。灾年来了到处都乱了,人手不够用了。”
“那他们怎么不一起去汀州府?再说了家大业大的咋连一个护院都没有。”
“周老说他种的什么什么药来着,己经第48代了,说什么他五岁就开始种了,就等它结果了。包袱都收好了,放在马车上了。准备收了种子就走的。”
“结果县城的城门被攻破了,那些流民一进来就冲着他们这些大户来了。本来周秀才身边是有两个武力高强的人的,那天守着前院对抗流民。其他护院只来得及把马车上的一些行李给他们拿下来,马车都不敢架了,就这么仓皇逃出来了。”
“护院都走散了?”
“护院都被冲散了,就跟了个药童。周老说他来这里也是临时决定的,原计划是去汀州府的,所以护院们可能都往汀州府寻去了。”
“哈,这俩人也忒不靠谱了点哈!那什么种子到底后面有没有收到呢?”
“收了,收了,收了一些,周老说的时候还拍大腿,一脸可惜呢!”
“阿禾,七婆跟你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这是没死的骆驼呢是吧,这可是妥妥的大金龟婿呢,你可得抓住了。”
“呵呵,阿婆我还小呢!”
“你还小?你都十六了。”
“啊~~七婆,我听出了你的嫌弃!”
七婆戳了戳阿禾的头道:“我们几个老家伙们都帮你相看好了,也商量过了,都觉得稳妥!
你可别扯后腿啊!难道你想嫁个老赖子那样的人?”
阿禾想到了村里的陈二狗,就是七婆说的老赖子,因为长得丑,个子矮,还不勤快。
天天东家串西家溜的。阿禾想到那个样子吓得抖了抖,赶紧摇头。
“七婆,那周大哥还是长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哈,就是弱了吧唧的,你不知道他路都走不好,走百步摔一跤的。”
“他是个少爷,能跟你们这些猴一样吗?”七婆说着就要打阿禾
“是,是,是七婆我吃好了”阿禾说着把碗一放,窜得比兔子还快。
“诶~诶!还没讲完呢!你跑啥?”
“我都知道了~”阿禾声音远远的传来。
“阿禾,你脸怎么这么红?”才出崖缝就遇到了周青峰,果然大白天的不能说人哈。
“嗯,我刚喝了一大碗的龙凤汤,热的。”
远处陈阿公蹲在木桶前,十指翻飞如揉面团,粗盐粒裹着红褐色的野猪肉簌簌滚落。
三阿婆眯眼穿针引线,把腌好的肉块挂上在树枝上,微风掠过时,整片树冠都晃动着琥珀色的玛瑙。
二十步外的树林里,两个后生正和碗口粗的树干较劲。斧刃劈入木纹的闷响带着奇特的韵律,断茬处溅出的木屑落在少年柴胡汗津津的后颈,惹得他边挥斧边缩脖子笑。
刚砍倒的树干被王婶子和春花都细细的劈去了枝桠,用一人高的木枝做成卡柱,把木头一根根的排进去。
偶尔插上几根短枝固定成木排,围栏己经有半人的高度了,空气里弥漫着树脂的香气。
“当心扎手!”小陈叔拎着半瘸的山麂走来,把挣扎的小兽塞进围栏时,麂子金棕色的皮毛蹭过阿禾的手腕,在阳光下泛起缎子般的光。
不知谁先哼起了猎调,剁肉声、搓盐声、伐木声忽然都有了拍子。三阿公抹了把胡须上的盐粒,看见三阿婆挂着肉块的榆树枝头,不知何时停了两只山雀,正歪着脑袋看树下一排排油亮的腌肉。
年轻人扛着新伐的木材从树林里钻出来,肩头的露水映着阳光,晃出满地细碎的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