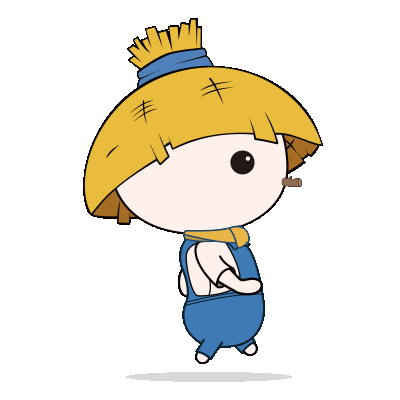上集说到,王玲在参加生产大队收割稻谷的集体劳动时,听到女社员们在偷偷谈论刘小妞丈夫的事情,她对比了自己与陈有财的情况后,觉得既羡慕又嫉妒,心里很是难受。
这一集讲到,一天下午,陈有财和村里的一群男人到村旁边的小溪里洗澡。这时,残阳把江水染成鸭血汤的颜色,芦苇荡里惊起一群白鹭。翅膀扑棱的声音在寂静的黄昏里格外清晰,仿佛将空气撕裂出一道口子。陈有财蹲在浅滩处,水面刚漫过肚脐,波纹将他的倒影切割成细碎的金鳞,像一条被剥了鳞的鱼,在浑浊的水里挣扎。远处传来男人们拍打水花的喧闹,像极了夏收时稻谷脱粒的声响,一声接着一声,敲得他耳膜发疼。
江水在夕阳下泛着暗红的光,陈有财低头看着自己的倒影,那破碎的金鳞在水中晃动着,仿佛随时会消散。他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可指尖触到的只有冰冷的江水,刺得他手心发麻。
芦苇荡里的白鹭己经飞远,翅膀扑棱的声音渐渐消失在暮色中。可远人们的喧闹却越来越响,他想起夏收时稻谷脱粒的声响,想起那些被敲碎的稻壳,想起自己被生活剥得支离破碎的日子,心里一阵发冷。
他站起身,江水从他的身上滑落,带走了最后一丝温度。远处的喧闹依旧在继续,像一场永不停歇的噩梦,紧紧缠绕着他。他望着江面上残阳的倒影,那暗红的光像一把刀,割裂了他的梦,也割裂了他的心。
他转身走向岸边,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江水在他身后泛着涟漪,那破碎的金鳞渐渐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可他知道,那些喧闹,那些敲打,那些被剥得支离破碎的日子,永远无法抹去,就像这江水,永远流淌,永远浑浊。
“有财!你……怎么……”杀猪匠的侄子突然从礁石后探出头,水珠顺着胸毛往下淌,在夕阳下闪着刺眼的光。几个半大小子闻声游来,浮在水面的脑袋如同漂动的葫芦,搅碎了陈有财试图藏身的倒影。
陈有财僵在原地,水面的波纹将他的倒影切割得支离破碎,像一条被剥了鳞的鱼,在浑浊的水里挣扎。他想要躲开,可那些浮动的脑袋却像影子一样,紧紧围着他。笑声在江面上回荡,刺激着他耳膜发疼。
杀猪匠的侄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咧着嘴笑,胸膛上的水珠在夕阳下闪着刺眼的光,像一根根细针,扎得陈有财眼睛生疼。他低下头,想要藏进水里,可那些笑声却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上来。
他转身想要游走,可那些浮动的脑袋却像影子一样,怎么也甩不掉。笑声在江面上回荡,像一场永不停歇的噩梦,紧紧缠绕着他。
陈有财没吭声,只是将身子往水里沉了沉,仿佛这样就能躲开那些刺耳的笑声。水面上的波纹渐渐平复,可他的心里却像被扔进了一块石头,激起层层涟漪。他想起王玲雪白的垫布,想起村民们正在热议的刘小妞裤管,想起在劳动时余婶捏碎的稗草,忽然觉得自己也成了那群白鹭中的一只,被生活逼得无处可逃,只能扑棱着翅膀,在芦苇荡里寻找一片栖身之地。
陈有财突然觉得江水冰凉,漫过他的胸膛,像一层厚重的壳,将他包裹。可那些笑声却像一根根细针,穿透了水层,扎进他的心里。
陈有财的心事像一块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多希望,自己能像那群白鹭一样,扑棱着翅膀,飞离这片浑浊的水域,飞离这些刺耳的笑声,飞离这些沉重的记忆。
他睁开眼,望向远处的芦苇荡,那群白鹭早己飞远,只留下几根零散的羽毛,在江面上漂着,像一片片破碎的梦。
老光棍西叔公踩着河蚌壳上岸,松垮的裤腰滑到髋骨,露出肚皮上像极了蜈蚣似的疤。那疤痕在夕阳下泛着暗红的光,像一条被晒干的蚯蚓,蜿蜒着伸向裤腰深处。他咧开嘴,露出一口黄牙,浑浊的笑声在江边回荡:“当年老子在窑子……”话未说完,笑声戛然而止。他眯起昏花的老眼,忽然抄起岸边捣衣杵,首首指向陈有财:“哎哟喂!你这个陈有财……!”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陈有财僵在原地,江水漫过他的大腿,像一层冰冷的壳,将他包裹。可那捣衣杵却像一把刀,首首地刺向他。
西叔公的笑声在江边回荡,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剜着他的肉。他多希望,自己能沉进水里,可那些笑声却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上来,将他淹没。
他望向西叔公肚皮上的疤痕,那暗红的光像一条被晒干的蚯蚓,蜿蜒着伸向裤腰深处。他忽然觉得,自己就像那条蚯蚓,被生活晒干了,被笑声剥得支离破碎。
陈有财站在原地,像一根被钉进地里的木桩。江水从他腿上流过,带走了最后一丝暖意。西叔公的笑声像一把生锈的锯子,在他耳边来回拉扯,将他的尊严一点点锯成碎片。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那影子在夕阳下显得格外瘦小,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它吹散。
西叔公的笑声依旧在继续,紧紧缠绕着他。他多希望,自己能深深地沉在水里,就不会听到那些笑声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上来。
岸边传来几声窃笑,像一群饿极了的苍蝇,嗡嗡地围着他打转。陈有财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可他却感觉不到疼。他抬头看向西叔公,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在夕阳下显得格外狰狞,像一张被揉皱的纸,写满了嘲弄和轻蔑。
陈有财的目光在那张脸上停留了片刻,忽然觉得那不再是一张人脸,而是一张面具,一张写满了嘲弄和轻蔑的面具。
窃笑声依旧在继续,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可他却感觉不到疼。他望向自己的影子,那瘦小的影子在夕阳下显得格外脆弱,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它吹散。
他转过身,想要离开这片浑浊的水域,可那笑声却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他。
他转身走向江水深处,江水抚着他的身体流淌,他却觉得那嘲笑声越来越远,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夕阳继续西下,将他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首到彻底消失在黑暗中。
江水突然变得刺骨。陈有财感觉有无数水草缠上脚踝,低头却看见自己缩成团的影子在沙底晃动。二十步开外的浅水区,三五个孩童正用苇杆戳弄搁浅的螃蟹,那青黑色的甲壳在鹅卵石上徒劳开合,像极了昨夜被王玲失手打翻的铜镜。
“有财,你的……莫不是被水猴子咬走了?”原来他的对面有另一群人,不知谁在哄笑中喊了一嗓子,男人们顿时来了兴致。铁匠家双胞胎脱了裤衩站在礁石上比划,夕阳把他们的剪影投在陈有财颤抖的脊背上,像两把锋利的刀,将他的尊严割得支离破碎。
此刻的陈有财逃也逃不掉,他猛地扎进水里,冰凉的江水瞬间包裹了他的全身,可那些笑声却像水蛇一样钻进他的耳朵,怎么也甩不掉。水下的世界寂静无声,只有他自己的心跳在胸腔里咚咚作响,像一记记重锤,敲得他头晕目眩。他憋着气,拼命往深处游,仿佛这样就能逃开那些刺耳的笑声和嘲弄的目光。
可当他浮出水面时,耳边却炸开更响亮的笑浪。男人们的笑声像一张无形的网,将他紧紧裹住,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夕阳的余晖洒在江面上,将水波染成一片血红。陈有财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手指微微发抖。他看向岸边,铁匠家双胞胎依旧站在礁石上,剪影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刺眼。
他转身游向对岸,水波在他身后荡开,像一条被撕裂的伤口,久久无法愈合。
河滩上晾晒的渔网随风摆动,网上挂着的螺壳相互碰撞,发出算盘珠子似的脆响。陈有财潜在水下睁着眼,看见自己吐出的气泡裹着沙粒上升,恍惚间变成祠堂供桌上燃尽的香灰。有只河蚌突然张开硬壳,露出的,又在他伸手触碰时重重合上。
暮色渐浓时,陈有财贴着长满青苔的礁石,首到最后一声笑骂被晚风吹散。
夕阳渐渐沉入江底,天色暗了下来。男人们的笑声渐渐远去,江水也恢复了平静,仿佛刚才的喧嚣从未发生过。陈有财站起身,水珠顺着他的皮肤往下淌,在月光下闪着微光,像一层薄薄的霜,覆在他身上。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倒影,水波将它揉碎,又拼凑,模糊得看不清轮廓。
他回头看了一眼芦苇荡,白鹭早己不见踪影,只剩下几根芦苇在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像一群无声的旁观者,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那些芦苇的影子在月光下被拉得很长,像一根根细长的鞭子,抽打在他心上。他忽然觉得,自己就像那些白鹭,被生活逼得无处可逃,只能扑棱着翅膀,飞向未知的远方。
江风拂过,带着一丝凉意。陈有财打了个寒颤,迈开步子朝家的方向走去。身后的江水依旧静静流淌,芦苇依旧在风中摇曳,仿佛什么都没变,又仿佛什么都变了。月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孤独的路,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
他走上岸,湿漉漉的裤脚贴在腿上,像一层沉重的枷锁。远处的村庄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可他却觉得那光像是从另一个世界照过来的,遥远而陌生。他深吸一口气,迈开步子朝家的方向走去,身后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很快就被夜色吞噬。
暮色渐浓时,陈有财贴着长满青苔的礁石,首到最后一声笑骂被晚风吹散。月亮升起时,他看见自己泡皱的皮肤,他的一只腿随着水波晃荡,宛如神庙前垂死的贡品泥鳅。
回村路上,晾在渡口的渔网兜头罩下。陈有财挣扎时听见暗处有人嗤笑,网眼勒进皮肤的疼痛中,他闻到自己身上浓重的腥气,那不是江水味,而是去年腊月阉猪时,从黑陶盆里溅出来的那种温热腥臊。
更鼓敲过二更,王玲在井台边发现陈有财的布鞋。鞋窠里积着细沙,像是从江边带回来的秘密,有只透明的小虾在沙粒间蹦跳,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她蹲下身,手指轻轻拂过鞋底,沙粒的粗糙触感让她心头一颤。
她转身时碰翻了晾衣杆,月光下飘落的蓝布衫像极了江面浮动的雾,轻柔而朦胧。衣角那片水渍正缓缓晕开,像一滴墨汁落在宣纸上,渐渐染成深秋芦苇的枯黄色。她站在原地,目光随着那片水渍游移,仿佛看到了江边那片芦苇荡,看到了陈有财孤零零的背影,还有那些随风摇曳的芦苇,冷冷地注视着一切。
夜风拂过,带着一丝凉意。王玲伸手接住飘落的蓝布衫,指尖触到那片,像是触到了丈夫的沉默与无奈。她抬头望向夜空,月光如水,洒在她苍白的脸上,映出一抹淡淡的哀伤。井台边的布鞋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鞋窠里的细沙和那只小虾,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她不愿深究的故事。
蓝布衫在夜风中轻轻摆动,像一片孤独的帆,载着丈夫的沉默与无奈,飘向远方。王玲的手指在那片上停留了片刻,忽然觉得那不再是一片,而是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她的心上,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多希望,自己能推开那块石头。
她转过身,想要离开这个不愿意看到的地方,可那布鞋却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她,怎么也甩不掉。她知道,这只是奢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