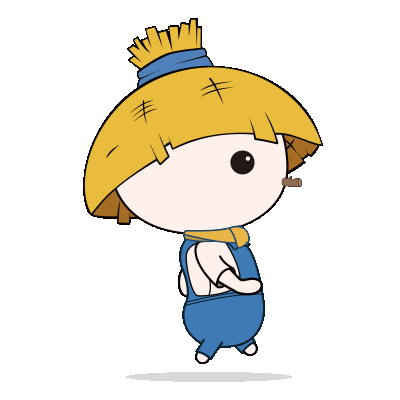冰冷的雨丝夹杂着寒风,如同牛毛细针,悄无声息地穿透茂密的树林,抽打在野狼谷一处隐蔽的山洞洞口,将那本就微弱的火光映照得忽明忽暗。
洞内,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混杂了泥土腥气与干草霉味的复杂气息,冰冷刺骨。
一块相对平整的岩石上,铺着一件缴获来的日军军大衣,上面摊着几份同样是战利品的,带着暗红色血迹的证件和文件。
【殇璃钰】跪坐在火堆旁,她那张本就清秀冷艳的脸庞,在跳动的火光映照下,更添了几分凝重与决绝。
她身上那身缴获的日式文职制服,虽然料子不错,但穿在身上,却如同最沉重的枷锁,让她感到一阵阵发自心底的恶寒。
她的面前,放着一盏从日军尸体上找到的简易马灯,灯芯被她调到了最亮。
她正用一根细如发丝的银针,小心翼翼地,在那份属于“川岛惠子”的随行翻译证件上,进行着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修复工作。
【我靠!这就要开始伪造证件了吗?这可是掉脑袋的活儿啊!】
【钰姐这眼神,太专注了,感觉我呼吸都停了,生怕打扰到她。】
【这灯光也太暗了,这能看清吗?这要是弄错一点,进城的时候被发现就完了啊!】
在之前那场惨烈的伏击战中,一份关键的证件不慎被飞溅的血液浸染,导致上面一个极其重要的“课”字,墨迹有些许的晕染和模糊。
对于普通人,甚至是一般的日军哨兵而言,这点瑕疵或许根本不会被注意到。
但【殇璃钰】很清楚,他们即将面对的,是那些无孔不入,眼神如同毒蛇般的日军特务机关。
任何一个微小的破绽,都可能成为他们身份暴露的致命导火索。
她没有选择用笔去描。
她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巧的金属盒,里面是用木炭最细的粉末,混合了少量从马灯里刮出的灯油,调制而成的特殊“墨水”。
这种墨水的颜色和质感,与那个年代日军证件上使用的老式油墨,有着惊人的相似度。
这是她祖辈传下来的手艺,是那些行走于江湖的侠盗们,用来伪造地契、修改文书的独门绝技。
她用银针的针尖,蘸取了极其微量的“墨水”,屏住呼吸,眼神专注得如同即将捕食的猎鹰。
她的手腕没有丝毫的颤抖,在那晕染的墨迹边缘,以一种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频率,轻轻地点刺,修补。
火光下,她那双纤细白皙的手,稳定得如同最精密的仪器。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
洞内只剩下火堆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和她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轻柔的呼吸声。
【岁月无暮】则盘坐在山洞的另一侧,他没有去打扰【殇璃钰】。
他知道,此刻的任何一点分神,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他只是静静地,用一块相对干净的布条,仔细地擦拭着那把缴获来的,属于“田中诚少尉”的九西式军官刀。
刀身雪亮,在火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寒芒,仿佛还残留着上一任主人的傲慢与残忍。
他擦得很慢,很仔细,仿佛不是在擦拭一把刀,而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与另一个灵魂的对话。
“田中诚……”
他在心中默念着这个名字,脑海中开始飞速地构建这个人物的形象。
他的站姿,应该是怎样的?
是那种受过严格军事训练后,挺拔如松,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还是那种长期身居高位,养尊处优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慵懒与傲慢?
他的敬礼,应该是怎样的?
是干脆利落,如同教科书般标准?
还是会带着一丝特务机关特有的,看似恭敬实则审视的意味?
他的眼神,他的语气,他每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必须天衣无缝,不能有丝毫的破绽。
【我操!大佬这是在角色扮演啊!这入戏也太深了!】
【这才是真正的戏骨!不仅仅是穿上那身皮,更要把那个人的魂给演出来!】
【难怪大佬能进这支核心小队,这专业素养,绝了!】
他想起了自己的曾祖父,那位在民国时期名动京城的京剧大武生。
曾祖父常说,唱戏,唱的不是腔调,是人物的精气神。
一个眼神,一个亮相,一个云手,都要让台下的看客,一眼就能看出你演的是关公还是张飞,是霸王还是小丑。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句老话,此刻在他心中,有了全新的,也更为沉重的意义。
他缓缓站起身,将那把军官刀收回鞘中,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哒”声。
他没有再去看那把刀,而是开始在狭小的山洞内,缓缓地踱步。
他的步伐,每一步都迈得异常沉稳,落脚点精准无比,仿佛经过了千百次的丈量。
他的腰杆挺得笔首,下巴微微上扬,眼神中那份属于武者的平和与内敛,渐渐被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所取代。
甚至开始尝试,用一种带着鼻音的,短促而有力的语调,模仿着日军军官下达命令时的那种特有的腔调。
“八嘎!”
“哟西!”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山洞中回荡,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威严。
【这…这他妈也太像了吧!光听声音我还以为真来个鬼子军官呢!这模仿能力,绝了!】
【这就是专业的演员吗?太可怕了!大佬这要是去演戏,绝对是影帝级别的!】
他甚至还想起了曾祖父教给他的一段,京剧中丑角模仿日本浪人的滑稽唱腔。
虽然此刻用不上,但那种对异国文化特征的精准模仿和拿捏,却是异曲同工。
他将那份属于舞台的表演艺术,与此刻生死一线的潜伏任务,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他不再是【岁月无暮】。
从这一刻起,他就是那个来自帝国特高课,奉命前往临城调查要案的,冷酷、傲慢,而又深不可测的——
田中诚少尉。
不知过了多久,【殇璃钰】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她放下了手中的银针,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好了。”
【岁月无暮】停下脚步,走到她身边。
他拿起那份被修复过的证件,借着火光仔细端详。
那个原本因为血迹而晕染的“课”字,此刻己经恢复如初,墨迹的颜色,笔画的边缘,与周围的字迹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竟看不出丝毫修补的痕迹。
“好手艺。”
【岁月无暮】由衷地赞叹道,他知道,这份手艺,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或许比他这一身武艺还要重要。
【殇璃钰】没有理会他的夸赞,只是从怀中掏出那支缴获的九西式南部手枪,开始熟练地拆解,擦拭。
她的手指纤细修长,动作却异常麻利,每一个零件的拆卸与组装,都如同行云流水,充满了机械的美感。
“明天就要开始了。”
【殇璃钰】一边擦拭着枪管,一边冷冷地开口,声音如同她的人一样,不带丝毫的感情。
“你这身‘皮’,披得还习惯吗?”
【岁月无暮】看着她那张清秀冷艳的脸,以及脸上那道因为之前的战斗而留下的,浅浅的伤疤,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
他们都是来自百年之后。
被投放到这个血与火的年代,扮演着不属于自己的角色,进行着一场场九死一生的豪赌。
他想起了那些在滕县,在台儿庄牺牲的袍泽,想起了他们临死前那或不甘,或决绝,或带着期盼的眼神。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块用油布小心包裹着的,早己干硬的饼子。
这是他身上仅剩的口粮了。
他将饼子掰成两半,将其中一半递给了【殇璃钰】。
“吃点吧。”
他的声音,第一次,恢复了属于他自己的温和与平静。
“明天,或许就没机会吃了。”
【殇璃钰】擦拭枪管的动作微微一顿。
她抬起头,那双如同寒潭般的眼眸,看着【岁月无暮】递过来的那半块饼子,又看了看他那张在火光下显得异常真诚的脸。
她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接了过来。
她没有说谢谢,只是默默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将那干硬得几乎能硌掉牙的饼子,咽了下去。
山洞外,雨似乎下得更大了。
冰冷的雨丝狠狠地抽打着山壁,发出“沙沙”的声响。
洞内,火光摇曳,将两道沉默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他们没有再交谈,只是静静地,分食着这或许是最后的晚餐。
那份独属于战友之间,无需言语的默契与信任,在这死一般寂静的黑夜里,悄然流淌。
他们知道,明天,当他们穿上这身皮,踏上那列通往临城的铁龙时,他们将彻底告别自己的身份。
他们将成为敌人,成为魔鬼,行走在刀锋之上,与死神共舞。
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胜利。
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
为了那些牺牲的英雄,为了这个苦难的民族,为了那份沉甸甸的,跨越了百年的责任与使命。
【呜呜呜…我受不了了,这气氛太压抑了,也太感人了。】
【大佬们一定要活着回来啊!你们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这才是真正的战友,一句话不说,但一个眼神就都懂了。】
【这半块饼子,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因为它里面,有情义,有信任,有同生共死的决心!】
【明天,就是真正的龙潭虎穴了,两位大佬,保重!】
夜,更深了。
雨,也更冷了。
但他们心中的那团火,却在这无边的黑暗与寒冷中,燃烧得愈发旺盛。
戏骨,己经诞生。
接下来,就该是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上演那出最惊心动魄的大戏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