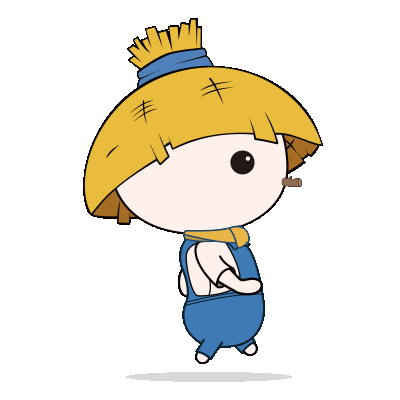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实际上,像我这样的泥瓦匠,面对一张详尽的图纸,只需仔细观察并动手实践一两次,就能掌握整个建造过程。”
“在其他同行还没来得及掌握这项技术之前,这种独特的单炉膛双锅灶台,只有我能够独立完成。”
“这样一来,我便有机会通过这项独家技术,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
听完赵建设这番充满自信的话语,苏童会心地点头表示理解:原来如此。
她亲自设计的这种单炉膛双锅灶台,确实耗费了她不少心血和时间,但若真的打算将这项“设计专利”推向市场,换取金钱,似乎并不那么切实可行。
毕竟,正如赵建设所言,只要泥瓦匠们亲自建造一两次这样的灶台,他们就能够逐渐掌握其中的技巧。
因此,这种设计的独创性和技术壁垒并不是特别坚固。
苏童深知,可能用不了多久——也许三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会有其他泥瓦匠通过观察和实践,学会如何制作这种灶台。
到那时,这项技术的独特性就会大打折扣,市场上可能会涌现出许多模仿者,从而使得这项设计的商业价值迅速降低。
赵建设的想法,实际上建立在对自身技能的充分了解,和对行业现状的敏锐洞察之上。
在建筑行业,技术的传播速度往往非常快,尤其是在像他们这样的手工艺人之间,经验的分享和技能的传承几乎是日常。
因此,他想要在其他人学会之前,利用这项技术为自已赢得一些经济上的优势。
苏童也清楚,赵建设的这种想法在建筑行业中并不罕见,许多工匠都会通过掌握一些独特的技术或工艺来提升自已的市场竞争力。
苏童深知,尽管他她的设计充满了创新和实用价值,但申请专利根本是不现实的。
在古代,这样的保护机制并不完善。
因此,她意识到,即便她的双锅灶台设计再怎么独特,也无法像现代那样通过专利来确保自已的权益。
赵建设看到了这个设计的潜在价值,并提出了一个看似对双方都有利的建议。
只要苏童愿意将双锅灶台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他愿意仅收取材料成本,而工钱则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的提议对于苏童来说,无疑是一个减轻经济负担的好机会。
“建设兄弟,”
苏童温和地说道:
“你已经给我打了折扣,我怎么好意思再让你吃亏呢?这个双锅灶台的图纸,如果你觉得它真的有用,那么你就拿去用吧。我并不需要额外的条款约束。”
赵建设听到苏童的话后,脸上立刻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他原本以为苏童会坚持给自已多要钱,没想到对方如此慷慨大方。
他急忙问道:“那苏嫂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垒灶台呢?”
苏童回答道:“当然是越快越好,今天就可以开始。”
赵建设一听,立刻兴奋起来:
“好嘞!我现在就去砖头厂,把垒灶台所需的砖头和材料都运过来。”
说完,赵建设便大步流星地离开了,他的步伐中充满了期待和动力。
他已经开始想象,这个双锅灶台一旦建成,将会有很多人请他来垒这样的锅台。
这时,一旁吃饭的赵大林已经吃完了饭,碗筷背在身后,一脸笑意地走到苏童面前。
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皱纹间似乎都洋溢着对苏童的赞赏。
“宣武娘,你画的这个东西,还真能行?”赵大林好奇地问道,声音中带着几分喜悦。
苏童则是一脸的得意,她自信地回答道:
“大林叔,你就算不相信我,也得相信建设兄弟的眼光吧,他可是你的亲儿子啊!”
赵大林哈哈笑道:“哈哈!要是我儿子建设真能用你画的灶台挣了钱,那今后俺家的牛车,让你优先使用!”
作为赵建设的父亲,赵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儿子现在的处境。
尽管儿子在建筑方面有着过人的手艺,但在这个荒年,盖房子的活儿并不多。
要论盖房子,这附近几个村子,就没有一个比自已儿子手艺强的。
然而,手艺再好,也得有活儿干才行。
虽说一技傍身,吃穿不愁,但眼下正值荒年,哪里还有几家农户盖房子的呢?
所以,家里的收入基本上就靠几亩薄田,还有自已驾着牛车,每天往返镇上,赚几个钱。这活儿虽然不是辛苦,但最多也是维持温饱罢了。
没人盖房子,可不代表没人垒灶台啊。
苏童的这个主意,让赵大林看到了新的希望。
一来,垒一副这样的单炉膛双锅灶台,成本不到300文钱,好多人家是能够负担的起的。
二来,这样的双锅灶台,实用性确实强,做饭的效率直接翻倍,谁能不喜欢呢?
垒一副这样的灶台,大概能挣90文的工钱,要是能垒个二三十副灶台,怎么着也能挣个二两银子了。
想想都让人心动。
这还多亏了苏童呢!
在赵大林的印象中,苏童在村里一直都是一个小透明的存在。
可没想到,接触了两三次之后,这个年轻的妇人,却是那么的不一般。
所以,自已家的牛车,优先让苏童使用也是情理之中的。农村人,肯定要讲个人情世故的。
告别了赵大林,苏童则是返回家中,准备把灶房的东西都收拾一下。
因为要重新垒灶台,所以,灶房里面的东西要全部清理出来。
………………
临安城,大景王朝都城,太子府。
太子秦渊正在兴致勃勃地把玩手里的琉璃杯。
这只琉璃杯,正是苏童在永泰当铺卖的那只高脚杯。
对于这个晶莹剔透的玩意,太子秦渊则是爱不释手。
“高雷高电,你们俩辛苦了。回去告诉你们头领高尊,他的心意,本太子心领了,日后,我会重重有赏!”
高雷和高电急忙抱拳:“谢太子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