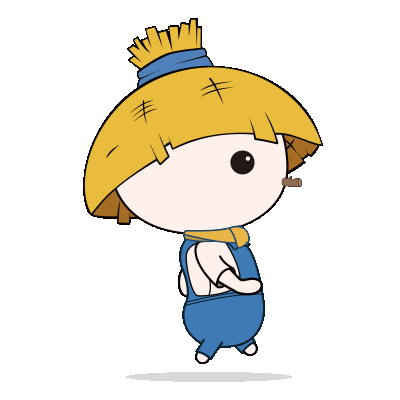火光映照在机器狗的金属外壳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院门燃烧的声音,惊动了钱翠花一家人。
众人傻傻地看着燃烧的院门,脸上写满了惊恐和不解。
“这……怎么会这样?院门怎么突然也着火了……”
刚才,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房屋上,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院门是如何在一瞬间被火焰吞噬的。
院门突然着火,这情景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像一层厚重的阴影,悄然降临在钱翠花一家人的头上。
苏童躺在床上,冷静地操纵着她的机器狗,随着她的指令,机器狗迅速点燃了整个院门。
火势迅速燃起,院门在烈焰中剧烈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时间不长,熊熊燃烧的院门就被烧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苏童没有停止,她继续操纵着机器狗,让它迈着机械的步伐,走进了院子。
通过机器狗的第一视角,苏童仿佛身临其境,她看到了院子里面的情景。
钱翠花一家人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显得惊慌失措,他们脸上沾满了灰尘,显得灰头土脸。
看到这一景象,苏童嘴角勾起一抹微笑:好极了!
“啊!!!”
突然,一声惊恐的尖叫划破了夜空。
钱翠花一家人看到一只狗,一只外表光滑、身上没有一丝毛发的狗,从那火门的窟窿中走了进来。
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得魂飞魄散,仿佛丢了七魂六魄一般。
下意识地,钱翠花紧紧握着手中的瓢,紧张得几乎要窒息,她颤抖着手指,指着那台逼近的机器狗,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恐惧和颤抖:
“我告诉你!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我可不怕你……”
“汪!汪汪!!汪汪汪!!!”
钱翠花狗叫了几声,试图把自已的话翻译成狗语,跟机器狗进行语言交流。
尽管钱翠花试图用坚定的语气来掩饰内心的恐惧,但她的身体却出卖了她的真实感受。
她的四肢不受控制地颤抖着,仿佛她整个人都变成了筛子,被剧烈的恐惧所筛动。
她的脸色苍白,眼神中充满了惊慌失措,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名状的恐怖之物。
这一切,苏童通过机器狗的第一视角看得一清二楚。她仿佛能感受到钱翠花的恐惧,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机器狗的下一步操纵。
苏童轻蔑地骂了一句:“老妖婆!”
然后继续操纵着机器狗,慢慢地、一步步地逼近钱翠花。
钱翠花被吓得连连后退,她手中的瓢也因为过度的惊恐而滑落在地。
机器狗则伸出右腿,轻轻地晃了晃,仿佛在用一种机械的方式向钱翠花打招呼。
钱翠花在本能的驱使下,也下意识地抬起右手,似乎想要回应这个不速之客的“问候”。
然而,就在下一秒,苏童按下了点火按钮。
瞬间,一团烈火从机器狗的铁管子中喷出,如同一条火舌,直接喷在了钱翠花的脸上。
钱翠花的整个脸庞,包括她的猪头,全部燃烧了起来。
“啊!啊……”
钱翠花痛苦地尖叫着,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回荡在整个村子。她拼命地用手拍打着脸上和头上的火焰,试图扑灭这突如其来的火海。
她的皮肤在烈火的炙烤下迅速变红,然后开始起泡,疼痛感如同无数针刺般穿透她的神经。
看到钱翠花的脑袋被点着了,旁边的老伴赵学高立刻反应过来,他以最快的速度冲进灶房,端起一盆水,毫不犹豫地浇在钱翠花的头上。
水与火相遇,发出嘶嘶的声响,但火势并未立即熄灭。
与此同时,钱翠花的儿子赵德平,慌乱中几乎失去了理智,他迅速脱下自已的裤衩,沾上水,然后盖在了钱翠花的脑袋上面。
父子俩齐心协力,终于将钱翠花燃烧的脑袋扑灭了。
然而,此时的钱翠花已经被急火攻心,她感到一阵眩晕,眼前一黑,便昏死了过去。
她的头发全部被烧光,只剩下光秃秃的脑袋,脸上、耳朵、鼻子、睫毛,整个头部都被严重烧伤,直接破了相。
皮肤上布满了水泡和烧伤的痕迹,看起来触目惊心。
此刻,作为肇事凶手的机器狗,早已消失地无影无踪。
不多时,苏童操纵机器狗回到家中,连同手里的平板电脑,一起放进了系统空间。
做完这一切,苏童再次回到床上。
今晚,肯定能做个好梦。
漆黑的夜,赵家的院子里弥漫着一股紧张而混乱的气氛。
钱翠花此刻正躺在地上,不知是死是活,她的头发被火苗舔舐过,显得凌乱不堪,脸上满是烟熏火燎的痕迹,看起来就像是被烧焦了一般。
赵学高站在一旁,看着老伴的惨状,他的心仿佛被撕裂了一样,彻底乱了分寸。
前日刚埋了大儿子一家七口,现在,他可不想再失去老伴。
“老三,快去镇上请大夫!快去请大夫!”赵学高焦急地喊道,声音中充满了绝望和无助。
老三赵德平,刚刚从这场大火中恢复过来,整个人还处于一种失神的状态。
他看着父亲,声音沙哑地回答:“爹!这大晚上的,咋去镇上?就算去了镇上,人家大夫也不会愿意上门的……”
老三的媳妇刘氏,怀里紧紧抱着两个受惊的儿子,她的眼神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她嘴里嘀咕着:“就算大夫肯上门诊治,咱家还有钱付诊费吗?”
家产都被烧光了,哪里还有半文钱?
赵学高气愤地捶了捶地面,高声喊道:“那就让你娘等死吗?啊!”
“你们两个不孝的畜生!是不是盼着你娘死了,然后你们俩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头子啊?!”赵学高的话语中充满了愤怒和指责。
老三媳妇刘氏听后,忍不住讥讽道:“我两口子不孝?公爹,你真是蹬着俩大眼说瞎话!”
“我们若是不孝,会让公爹公婆跟着我们生活?我家养了你们老两口这么多年,反倒落个不孝,这还有天理吗?!”刘氏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委屈和不满。
赵学高气得咬破了嘴唇,开始破口大骂自已的儿媳:
“你个贱妇!这些年,我两口子少干活了吗?家里十八亩良田,有十二亩都在我两口子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