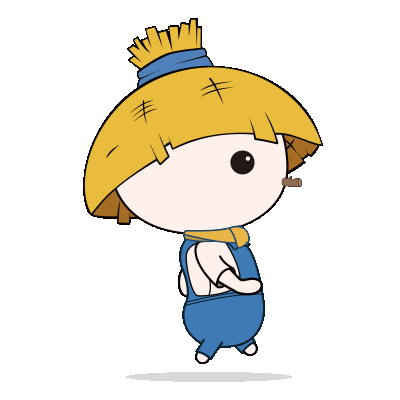张叔拉着何大清往边上去了去,不知道两人在嘀咕什么。一个在不停的说,一个在不停的点头。
易中海师徒两人见没人理他们,便往中院走去。只是,边走边侧头看向已经属于常庆的房子。两人嘴里似乎还说着什么,只是离得远又太小声,常庆就没有听到。
常庆看着这两师徒,不用动脑子都知道,他俩是在打房子的主意。
闫阜贵依旧在打理着自家的花草。毕竟,小东西可以算计,房子这种东西太难了。所以,闫阜贵干脆不靠过来。
“庆哥儿,到外面转角的铺子再添份酱牛肉和烤鸭。今儿晚上跟你何叔一家熟悉熟悉。”跟何大清嘀咕完了的张叔,转头就向常庆吩咐到。似乎有晚辈不使唤会亏了一般。
“叔,今儿个不成,我老常家今儿个新喪,不能坏了规矩。拖累了何叔。”常庆大声且有力的说道。这个时候只能大声说出来,不然两个人到旁边嘀咕,最后让别人以为是小气还是怎么的。常庆刚顶门立户,可不能让老常家门楣低了一等。
何大清看了眼常庆,又定定的看着张叔,似乎要个解释。
于是,张叔拉着何大清又往一边嘀咕去了。
不知道两人又说了啥。总之,等何大清往中院走的时候,看常庆的眼神里带了一丝怜悯。
狗日的何大清,可怜谁呢!等明年谁又可怜你何家两个孩子!常庆撇撇嘴想道。
唉,到时候看在张叔的面子上,提一下傻柱,他老子有给他留工位,钱,以及每个月都寄钱的事儿吧!谁让咱常庆是个好人呢。
“叔没跟谁提起你给娄家上工的事儿,就说了你家老爷子今儿个没的。”张叔一边坐着看常庆在摆弄吃食,一边跟常庆说道。
“叔怎么说都行,来,我敬叔一杯。大恩不言谢。”常庆说着举起了装满酒的杯子。
张叔提起杯子一口干了对常庆说:“叔明儿一早就奔天津去了,本想着今儿给你介绍一下老何,好让他在院里多照顾你一下,别被人给欺负狠了。”
“谢了,叔。其实,我不怕的,有功夫在身呢。再说了,明的暗的这些年跟着老爷子也见不少,这小庙翻不起大风浪。”
“哟,你小子倒是年少轻狂,哈哈!行,各人有各人的缘法。叔相信你能过得好。答应叔,赶紧娶个媳妇,给老常家开枝散叶!”张叔边说边扯了个鸡腿,估计是下午哭得狠了,累的。而且,赶马车也是个力气活。
“得咧!”一直到夜深,两个人连两瓶酒都没喝完,一个是明天赶路,怕耽误事儿不敢多喝。一个是受伤不被允许多喝!烧鸡倒是吃得干净,毕竟什么年代肉食都是精贵的东西。
叔侄两人一起将就的躺在一张破床上酣睡过去,就盖了张破棉絮。不久就响起了鼾声,大约都是累了!明天起来没冷死,估计都是酒的功劳!
前院,一片寂静,还能听到不知名的虫子发出的声音。
中院东西厢房虽然吹灭了煤油灯,似乎里面的人都睡了。但细细听来,还是可以听到里面正在热烈的谈论着什么。
后院这个点还传来孩子的哭声,多半是刘海中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在打他的孩子吧。当然,仅限两个小的,长子是一个手指头都不碰的。
凌晨时分,不知道是酒喝多了被尿憋醒,还是被子被扯走而冷醒的常庆,一脸无语的看着卷着被子的张叔。随即出门打算找个地方拉尿…
走出家门才想起,自已不知道这边的厕所在哪里。于是,几步走到闫老西那几盘花花草草。就地减轻负担,盘盘都雨露均沾。
转身回屋,干脆不睡床上了。把堂屋的桌椅拉到门口,靠着门趴着继续睡。
常庆是被张叔敲脑袋敲醒的,对,就是敲。“你小子,人不大心眼不少!就这么怕张叔不告而别?”
常庆努力睁开朦胧的眼,看着眼前有些气恼的张叔。瞬间笑了起来:“您要不是被侄儿堵个正着会那么生气?”说完常庆就往棉大衣的口袋里掏东西,实际上是从系统空间里拿小黄鱼。
看着眼前常庆掏出放在桌上的十根小黄鱼,张叔眼角有些抽抽。手往前伸了伸又快速的收了回去!久久没有言语。
“拿着吧叔,穷家富路,这就当侄儿的房钱了。如果多了,就当侄儿孝敬叔的。如果少了,就当侄儿欠叔的。老常家所有的家当都在这了。”常庆虚虚实实的说道。毕竟,不能真的一点退路都不给自已留。
多是肯定多了,一根小黄鱼31.25克。十根那就是312.5克。外面十万一克都有价无市。不过常庆刚过来,什么都不了解。
“孝敬你个头啊!自已留着赶紧把老常家发场光大才是正事儿!你这根独苗可担着大责任呢!”张叔眼睛略带不舍的从黄鱼上移走。
“就凭您在我家老爷子坟前哭成那样,给再多我都愿意!”狗东西常庆漂亮话不要钱一般说着。
“以后不许再提起这事儿!”张叔面目略带狰狞的恐吓道。毕竟,谁都不愿意更多人知道自已的丑态。
常庆拿起桌上的黄鱼一把塞进张叔的怀里说道:“拿着吧,我们两家的情谊难道还不值这点阿堵物吗?您不拿,我以后都不好意思再见您了!”
张叔半响没说得了话,脸上尽是挣扎。常庆认为光这个挣扎的表情就值得这些黄鱼!
“收拾收拾,我们出发吧。把您送到车站我还得回来补个觉呢,一晚上没睡。被冷醒了!”常庆故作轻松道。
谁知道换来张叔一个香港脚,常庆差点没被踢倒。最后,张叔还是收下了黄鱼,或者说收下了这份情谊。
还是昨天那辆马车,似乎早早的停在了院外。不过赶车的换了个人——你不能指望马车自已回来不是,人都去天津了。马夫叫王迅,张叔几十年的老伙计了。能从战乱时期几十年陪伴过来,是真的不容易。毕竟旧中国每天都在死人。幸运的是常庆穿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新中国了!
天还没大亮,马车慢慢行走在有些颠簸的路上,一晃一晃的。一路上三人有一句没一句的搭着话儿。
不过,大多数都是常庆在说,另外两人在听。就听常庆以在娄家听到的消息告诉张叔:在香港应该找个靠山,比如吕乐,比如李超人,比如霍先生…再告诉他在香港应该多买房子土地,万不得已不轻易卖出去——当传家用…
丰台火车站的月台,和朱自清先生的月台很不一样。既垮不过去,也没有橘子在卖。常庆终究还是送走了唯一一位记忆中对自已好的故人。
回程的路上,车夫和乘客都默契的没有说话。只是等回到四合院,常庆说要给车钱的时候,被那精瘦的马夫甩了一鞭子。被打的还没骂出口呢,打人的骂骂咧咧的赶着马车走了。
常庆摸摸被打的地方,想着有多疼呢,谁知是被那可恶的马夫耍了。那是一下响鞭,光响不疼,吓唬牲畜的…心里默默的给马夫记上了一笔。下次去正阳门那买个烧鸡,必须跟王叔好好喝一顿。
院里该上班的,上学的都已经出门,剩下的不是老娘们就是小屁孩。谁都没搭理,开门进屋,再锁上门窗,往床上一卷那破棉絮,闭眼睡觉。谁来都不能吵吵!
睡梦中好像签了个到。只是怎么都看不清得到了什么东西。怎么看都看不清,常庆索性不管了,继续深度睡眠。两辈子了还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最终常庆还是被冻醒了,这破棉絮还是顶不住四九城初春的寒。家里手上也没个钟表,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反正醒了,得出门填饱五脏庙,还得买上几床上好的被子,床也得换,家具得添,厨具碗筷得添…常庆越想越气,因为他最后想到干脆把房子重新装修成后世的样子,起码有个洗澡的地方,一天不洗都不习惯…这样需要的钱就多了,他钱不够所以生气了!
在外面吃了两份焦圈加豆浆,混了个八成饱,豆汁是打死都不碰的。至于为什么大中午还有早餐吃?老板手艺潮…反正常庆的南方胃吃不惯!
跟着店老板的指示,找到了卖被子的地方。在跟店伙计一翻深入浅出的交流后,常庆肉疼的掏出了两百万。一共买了两床上等棉的被子,还有一床垫被。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伙计帮忙送货上门。约定了上门地址和时间,常庆继续他的掏钱肉疼之旅——毕竟吃饭不能没有碗,喝水不能没有杯子。
路过裁衣店的时候,顺带进去跟裁缝定了条锦旗。等着过了老爷子头七给君委会送去。
“人民英雄,国家卫士”八个大字,“常庆赠”三个小字。一条锦旗加11个字花了三十万。京城居,大不易啊!
铺好刚买的被子,常庆又往被子里钻。四九城初春的寒,还是没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