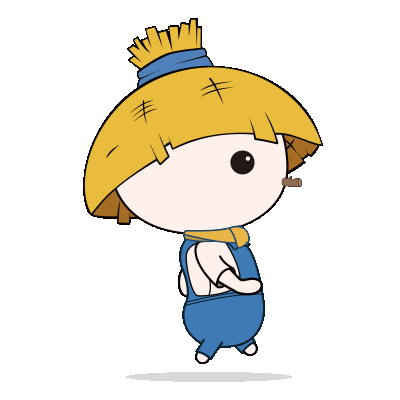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嗯,我知道了,医生,我现在精神状态十分良好。”
“感谢您给我的机会。”
颜良此时正在办理出院,他的父亲只是默默地站在他身旁,眼泪止不住地流。
出院之后,颜良打算脱离这繁忙的竞争,以后只要是遇到其他“玩家”就避开,
“我可不能因为这场荒诞的游戏把人生给搞砸了。”
恍惚之间,他又想到了自已高中时的事情。
当时不好的事情却发生了,自家的父亲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导致高位截瘫,腰身以下的部位全部瘫痪,还有很严重的烫伤。颜良打算退学去陪自已的父亲。
可是有一位同学知道他的事情,他的一位朋友。
“你为什么非得退学?”一位女生拉着颜良的衣袖,眼睛直直地盯着他。她是他高中时谈了两年的女朋友。
“哎呦,没钱交学费就退学咯,爷走了!”我本想踱步离开。
身后又是一句话:“你贫困生补助呢?”
“我拿去给我爹治病了,我干什么啦!”颜良冲她吼道。我看见她的眼角微红,不知道在想什么。
眼前的人忽然沉默地低下了头,眼睛不敢直视他。她似乎有泪要流出来。
我想安慰她,“别难过,这就是我这种人的命……”
这时候我看见她高高垒起的书上有糖,是她平时很喜欢吃的大白兔奶糖。我用手捏起了一颗,说:“别难过,拿你块糖吃,走了。”
转身离去,没有任何的犹豫,生活的压力不允许我回头,这一刻,一点也不潇洒。
不知多久后的一天,我照常的在废品站捡着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天气还是有点冷,我裹着厚重的衣物,手套已经很脏污,一双脏鞋被我塞进麻袋,我很庆幸没有遇到其他玩家来袭击我。
直到一个人影走了过来,米黄色的毛衣,白色的打底裤,那双白鞋,那乌黑的长发,外套下灰色的毛衫,以及那熟悉的脸庞,我抬起了那低下的头,是她,那日的红霞仿佛还未消散。
“你,你来干嘛?”
我能看见她的眼神有些飘忽,不敢直视这个污浊的我。
她用那纤细的双手递来一个信封,厚厚的一叠。
“给你学费,你跟我回去上学……”
我看向了她递过来的双手,下意识的接了过来,里面红彤彤的一片。
“你哪来的钱啊,偷你爸的?”
她此时就用手梳理着头发,或许说她不想让我看见她的脸。
“哎呀,你赶紧还回去!别打扰我干活,走走走走走!”
顺手将那个信件塞回了她的手中。
她一脸惊讶的看着我。
“你干嘛呀,这些钱我现在还不起了,我爸还住着院呢。”
“我给你还行不行?我让你还了!”
“你不是学生啊?你怎么还啊!”
“我现在在这挺好的,一天都有几百块呢,我现在……”
我本想继续说下去,但我看见了她递过来的东西。
“吃不吃?”
这是一句简单的询问,我看清了,是那日一样的大白兔奶糖。
她的眼神好像有点怕我,但我也不想拒绝学业。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顶住各方的压力给予我支持的,同一所高中内,我和她一起备战高考,周围的人也能看得出我们形影不离。
结果是喜人的,又是悲伤的,我们都考上了大学。
那一日,她站在天台上,微风吹拂着她的发丝,阴阳怪气地说,“你考上大学了,不得感谢我鸭,”一脸的洋洋自得,还有些羞涩的捋了捋耳旁的发丝。
“可是我的大学和你的大学距离有1000公里呢。”我失落的说道。
她转而一笑,“你就不怕我到了大学不理你了呀,嘿嘿嘿。”
“你欠我钱呢,你不理我,我报警抓你啊,你别上了你,哎!”
说完,挥舞粉拳,轻轻的打在我身上。
“那到时候咱们俩异地,你怎么管我呀,怎么管我呀?”
“人家异地是形容异地恋的,咱俩这种关系算不上什么异地,好吗?”她洋洋自得的捋着发丝,斜着眼看着我,声音拉的很长,随后又了嘴,我和她静静的看着湖面映射的夕阳,以及湖对岸那林立的高楼。
只是轻轻的回了一句,“哦。”
转头我看向了她的侧脸,问道,“你有没有糖?”
她装作一脸惊讶,“有啊,不过我这只有一块。”很得瑟的说,随后,她双手拆开大白兔奶糖的糖纸。
“想吃啊,我的啦,”她故意夹着嗓音说道。
随后,将那大白兔奶糖推进嘴里,整个人表现得很兴奋,摇头晃脑。
我也很犹豫,但那句话还是说出了口,
“那个,我也想吃……”
我将其轻轻搂进怀里,她的发丝挡住了我的视线,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更近了。
多日之后,我跟她发起了视频聊天。
几句闲聊之后,我抛出了我的目的,“我给你准备了惊喜。”
“啊?我,我明天坐最早的一班车去找你。”她有些口吃地回到,视频中的她正躺在床上,捋了下发丝说道,“嗯,你准备接驾啊,我给你带糖啊,依旧是熟悉的大白兔奶糖。”
“啊,好嘞,宝贝。”
这时我那留着蘑菇头的舍友也听到了这些,他戴着眼镜,一脸不可置信的贴近我。
“哎呦!”他大声的哀嚎,周围的几个室友也全听见了这对话。
“好嘞,宝贝,好嘞宝贝,好嘞宝贝,好嘞,宝贝。”
几个室友全在那叫唤,贴在我身旁,让我的手机有些晃荡。
那一日,我在Z市的地铁站与她道别,她把头发盘于脑后,很干净利落,
“我不想回学校,我不想离开你,烦死了。”她拉着我的手说道。
“那要不你晚点再走呢?”她只是用幽怨的眼神盯着我,开口道。
“这是最后一列班车了,我明天早八的课,要不然我今天怎么会走啊?”
我这时候想到了之前的情景,也夹着嗓音说,“那你吃块糖不就不难过了,好不好?”
“不好,我难过。”
“嘿,那我送你个这个呢?”
我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个礼物,是一个简朴的手链盒。
“你给我礼物呀,我们都是学生,你不要乱花钱。”
“这个不贵的,一对才100出头,你看我这边还有一个,”我举起了手中那同款的盒子,对方的是红色的,我的是绿色的。
“嗯……今年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呀,我想让我爸爸妈妈见见你。”这时候她还有些害羞的对我比了个心。
“啊?!”我有点怀疑我听错了,可她没有继续说下去,转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天上。
在假日的时候,我提着一盒礼物来到了他们家门前,当时是虎年门帘上的形象很可爱,一切都洋溢着喜庆的氛围。
我本想伸手去敲响房门,但房间里传来了吵闹声。
“为什么要让他来?你也不能跟他在一起!”
“凭什么我就和他在一起,怎么了?!”
“就凭他妈死的早,他爸还留下残疾,家里没有钱!他就不配和你在一起!”
我心中颇是苦涩,那份礼物被我放在地上,是一瓶酒,廉价的酒,我看向了它。
但一个尖锐的女声却是传了出来,“我要你管啊,我自已的事啊!”我的心里不禁一抽。
“哎呀,我还管不了你了,是吧!”就在这话说完的时候,门被推开了。
我与她直愣愣的,目光对视。
我看见了一个中年男人愤怒的目光,那有点发福的圆脸,责问声被堵住了,他也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我。
我的嗓音有点沙哑,我不清楚是不是因为自已感冒了,“额,不好意思,我外卖送错地方了。”
外卖送错地方,顺手我将那打开的门关上了,默默地提起地上的礼物,我离开了这栋单元楼。
我与他发生了很多矛盾,就在那件事情过后,我知道我认清了与她的差距。
争吵持续了一个月,冷战了一个月。
新年也在我们互不理睬中悄悄溜走,终于,我还是决定鼓起勇气跟她道歉。
那一日,公园的路灯昏黄,将那天上落下的雪照得很清晰。
我捧着一大束鲜花,这是纸做的,上面被我洒下了许多大白兔奶糖,还是那熟悉的房门,我重重地呼出热气,又吸了一口冷气。
这一次,我鼓起勇气敲响了房门。
脚步后移,防止打开的门撞到我,我的目光又放在了那束鲜花上,开门的是一个阿姨。
“哎,阿姨,那个孙艺桐在家吗?”
“搬走了,早搬走了。”
“搬……搬走了?”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手中的纸花。
“小伙子,还有什么事?”
“没事,没事,没事了阿姨,打扰您了。”
我回到家中翻看了那本日记,我和她一起写的日记,好像少年的故事总是这样,往后的每年,无论我在何方,我都会回到此地来,那一次亲吻她的天台上。
而今年是我们的第九年,我又来到了那天台上,我报的是艺术系的,支起画板,我准备画一幅画。
潦草的线稿勾勒出一副身影,一个戴着耳机的少女,长发及腰,我不禁思索,那时她长什么样子来着?
可看向身旁的座椅,那里空无一人,我不禁思索时间过去太久了吗……
身旁的咖啡一口没动,我得好好想一想,在熟悉的公园路径下,我想走一走,这说不定可以让我想起来。
走到身边的路灯亮起,走到那熟悉的天台,我重新拿起了碳笔,那潦草的线稿被画完了,熟悉的人脸再次浮现在我眼前,那戴着耳机的少女似乎有了神采,我被震撼到了,不知道是谁画的。
可那阴影笼罩的台面之上,我看到了一颗大白兔奶糖,我感觉泪要流下,一个穿着黑衣的妇女站在一旁,面容依旧秀丽,她的脚边是一个还不及她腰间的小女孩,
繁华的城市灯火通明,远处的高楼不再是生活中的信标,我所看见的只有自已脚下那被灯光晕染出的一片净土,这是我所立足的一片家园。
她开口了,“画,我帮你画完了。”
“小宝都想你了。”
“爸爸,我饿了。”
哎呦,我压抑不住心中的笑意,走了上去,
“饿啦?走,我带你去吃饭,好不好?”
我蹲下身形,牵着她的小手在那摇晃。
“画不要了?”小女孩疑惑地问道,这雪还在下,不担心画被毁坏?
“画……留着吧。”
我转头看向了那画中的人,面容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走喽,吃饭去喽。”
我和妻子一同牵着孩子的手,开口问道,“老婆,是不是该给你补办个婚礼了?”
“怎么突然想补办个婚礼啊?”
“当初你跟我偷偷领了证,那个时候我就欠你一场婚礼。”
“再说我们认识到现在,已经九年了嘛?”
“嗯,那什么时候啊?”
“嗯,那就明年今日。”
“好……”
寂静的街角路灯之下,只剩一家三口行走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