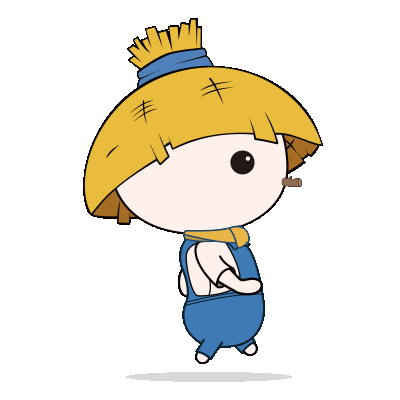晚上七点十分,我的航班落在了梁溪机场的停机坪上,关闭飞行模式,打开微信,第一条便是宋以柔的消息。
【陈默,我已经到了,你落地后给我报个平安!】
于是我顺手回了一个:【已安全到达,勿念!】
一分钟不到,宋以柔就回了过来:【我正在跟团队开公关会议,你回家后记得吃饭,我忙完告诉你。】
今天的梁溪也在下雨,不同海南的温暖,这是刺骨的寒冷,我点上支烟,拉着行李箱冒雨向停车场走去。
此时的梁溪早已融入无尽的黑暗之中,可我却无比眷恋着这片黑暗,因为它提供了我唯一可以躲藏的栖身之所。
我重重地抽了最后一口烟,两指用力一弹,烟头在黑暗中划出了一条火光色的抛物线,落在了不远处的水坑里。
将行李箱塞进后备箱,我便驱车向家驶去,路上我又再次想起了周菱,不知道她现在还好吗?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周菱在沙漠时有振振词的跟我说道:“陈默,你一定记得,我家就住在静海市百湖镇莲花东路195号,如果有一天找不到我了,你一定记得来这里找我。”
从那日,周菱与我在机场分别已经过了一周多了,我们没有联系过彼此,我猜测她应该还在沙漠冒着严寒拍摄着她的纪录片,或者整个摄制组此刻正围篝火在帐篷内载歌载舞,那个刻在脑中的地址又一次跳进了我的脑中,我不知道她拍摄完是否会回到那里,我也努力不去想这些,因为一切都不再重要了,因为我要跟另一个人女人开始我人生新的旅程了。
……
回到家中,我给老妈去了个电话报了平安,不免又再次被她问及宋以柔的事,我胡乱找个理由搪塞了,这一切太快,就像一场梦,而这个虚幻的梦,当下我又如何敢呈现在她们的面前。
看得出来,夏天只是喂了喂鱼,其他什么也没有做,看着鱼缸中游来游去的小鱼,我莫名的想念宋以柔,想念她的味道,她的拥抱她的吻,幻想着她穿着一身洁白的羽绒服站在我的面前,我们就这样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着鱼缸中那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这种情绪被无限放大后,我开始坐不住了,拿起水壶为阳台上那些稍有干枯的绿植浇了浇水,我将屋内所有的窗户打开通风,瞬间整个屋子被寒流侵占,在手脚还未失去温度之前,我拿起抹布拖把给整个房子打扫了一遍,最后关上窗子,躺在沙发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也许是昨晚没有睡好,也许是早上的吵闹太过耗费精神,躺在沙发上眼皮竟开始变得有些沉重,昏昏欲睡之际,手机铃声将我从迷糊强行转成了清醒。
黑暗中,我吃力的起身看了眼茶几上发着亮光的屏幕,是楚汉文的电话。
我接通了电话,点开了扬声器,他那边有些吵闹:“陈默,你回来了?”
“你在我头上装天网了?”
“没有,前面正好有事问冰姐,她提了一嘴,说你刚刚到家。”
楚汉文的语气满是热情,我不愿打破他的这份热情,于是解释道:“到了一会了,太累了,就想着明天再跟你们说来着。”
“出来吧!我和司徒北夏天在小峰饭店呢!让他们跟你说啊!”说着我听到了司徒北的声音:“默,过来吧!我让你看看我的草图!”
我本想拒绝的,坐飞机本就是一件累人的事,但又不知该如何回绝他们,于是便硬着头皮应允了下来。
我没有打算开车,换了件黑色的羽绒服便走出了家门,对门的江虹家毫无动静,我轻轻摸了摸她家的门把手,上面有些许落灰,想必为了避开我已经好久没有住在这里了。
……
外面依旧寒雨纷纷,我打了个车直接向市里赶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南长街变成了外地游客们打卡的必经之地,所以晚上这个时间段非必要我们是不愿意开车来这里的,堵的让人怀疑人生,我让司机将车停在了对面。
看了看远在两百多米的红绿灯,又伸手感受了浓密的小雨,于是翻过护栏的念头在心里油然而生,然而一分钟后我就会后悔这个决定,可这个世界中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后悔药。
我见没有车子便一个箭步冲到了马路中间,一手拉着湿滑的护栏,右腿一抬翻了上去,然后我低估了护栏的湿滑,一个没站稳摔了过去。
随后我便听到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摩擦的声音,随后是剧烈的疼痛感席卷全身,我看到自已飞了出去,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我躺在地上,脸部跟沥青路面产生了猛烈的摩擦,路面上凸起的尖锐小点划破了我脸部的皮肤和嘴角,我几乎可以闻到鲜血透过皮肤的气味。
我试图想要起身,然而自已仿佛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任凭我如何努力都动弹不得分毫,一时间,汽油味、血腥味、雨水味、还有远处远处饭店的饭菜香气都随着寒风一股脑的飘进了我的鼻腔。
我看着远处商场顶端的广告牌,黑夜中它是那般的扎眼,仿佛在嘲笑着我这愚蠢且无知的行为。
不知道这样躺了多久,我感觉眼前光线一暗,一个黑色的人影走到了我的面前,黑暗中,那两排白森森的牙齿是那样的扎眼且不合群,我听到了一个略显紧张的声音。
“朋友,你没事吧?”
我看不清他的样貌,通过轮廓大概能辨别是个中年男人,我在心里咒骂道:“你TM试试?要是你估计早废了!”
可惜我只能在心里说说,因为我发现自已除了意识是清醒的,竟然说不出话来。
不多会我能感觉边上围满了人,各种吵闹声在我耳边响起,直至那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去你M的,是陈默!”这是楚汉文的声音。
“快打120,赶紧打!”这是夏天的声音。
“你TM哪也别去,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开的车。”我听到了司徒北的咒骂声。
“他忽然就从护栏上跳了下来,我已经紧急刹车了,根本来不及……”这是先前那个男人解释的声音。
之后我的意识开始变的模糊,直到耳边变的清净,我便失去了所有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