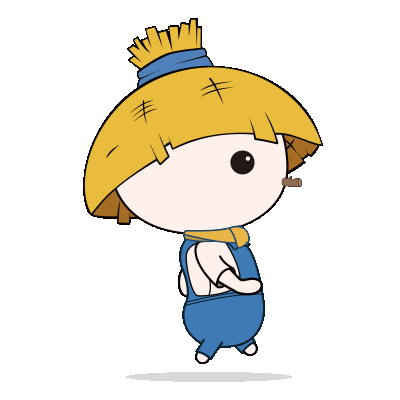白大太太看他们落荒而逃,忍不住想笑,“还是那么怕你。”
霍珝:“那是他们胆小。”
顿了顿又道,“霍钧就不怕。”
白大太太:“......他还像以前?”
霍珝简洁地道,“对。”
白大太太眉间染上轻愁,沉默了会儿才道,“打也打过,骂也骂过,怎么就改不了。”
霍珝答道,“天性。”
霍钧是他二弟,从小就热衷于与他作对,什么都跟他比。
比不过就出阴招,明明也是大家子弟,却能用出下三滥的手段。
如果不是怕老头子伤心,他不会容忍,霍钧坟上的草都有半人高了。
白大太太叹了几声,压低声音道,“阿珝,不要手软。只要不弄死,你爹也不会怎样。”
她承认,她偏心阿珝。
但她怎能不偏心呢?
阿珝的母亲,是她闺中密友,和她亲如姐妹,去世前拉着她的手,求她看顾儿子,得到她的承诺,才闭上了眼睛。
其他侄儿、侄女们的母亲,就只是姨太太而已,虽然她一样是姑母,也分个远近亲疏。
何况,霍钧这小子,也着实不像话,小时候就懂得砸碎大哥最喜欢的鼻烟壶,嫁祸给阿珝。
长大更是会偷姨太太的贴身之物,藏到阿珝房里,诬陷阿珝与姨太太有染。
大哥也不是没有严加管教,鞭子都打断了几根,他还是屡教不改,又不能打死,也是烦恼得很。
也许阿珝说得对,这是天性。
霍珝感受得到她的关爱,温声道,“姑母放心,我心里有数。”
看一眼许弦声,状似不经意地道,“表弟妹初次来我家,还习惯吗?”
许弦声正凝神听着霍家的豪门恩怨,没想到他会忽然跟自已说话,愣了下才道,“习惯,多谢大表哥。”
霍珝:“不客气,若有不周之处,还请表弟妹见谅。”
许弦声心想你叫我不客气,你自已客气得我都不知道怎么答话了,唯有点头称是。
白大太太看出她尴尬,笑道,“都不是外人,随意些。”
霍珝问道,“姑母,承璟去哪儿了?”
下楼时他就环视了一圈,那糟心表弟不在。
提起长子,白大太太也觉心塞,“谁知道野去哪儿了,说是朋友相邀,推不得。”
白大老爷怀疑儿子是去勾栏听曲,颇感羡慕,不以为然地道,“男儿在外,总有些应酬,知道回来就行。”
白大太太冷哼一声,心里有无数话可以反驳,但当着晚辈们的面,不好多说,免得他们以为长辈吵架。
霍珝又看了许弦声一眼,不再说话。
许弦声:......看我做甚?你那表弟我可管不了。
午饭也是在行风楼吃的,同样很丰盛,樱桃肉专门摆在许弦声面前。
她暗赞霍家下人周全,却不知这是霍珝的叮嘱。
吃完饭,白大老爷借口拜访老朋友,也出去了。
白承玮和霍十少交好,之前就说定了要去看他新养的金鱼,白宝婵也想看,姐弟俩一起去少爷小姐们住的小西楼。
霍家庄园主建筑分为四处,霍大帅带着姨太太们住在主宅,左侧的行风楼住了霍珝,右侧的小西楼住了八岁以上的少爷小姐。
庄园东南角另有一处宽敞的两层楼房,是霍家父子办公之所,卫兵日夜值守,霍大帅命名军机处,霍珝没他那么狂妄,觉得自家压不住,改为东南楼。
来霍家之前,白大太太就特意交待过许弦声,主宅和小西楼都能去,但东南楼不可靠近。
许弦声牢记在心,打定主意跟紧白大太太,别说东南楼,主宅和小西楼她也不单独前往。
那三人一走,行风楼花厅里就只剩了白大太太、许弦声、霍珝。
白大太太笑道,“阿珝,你忙你自已的,不用陪着我。”
她午饭后有休息的习惯,现在还没回房,是约了装炕屏画的师傅,要挑个好样式。
儿媳绣好了炕屏画,但框架总不能从闻桐城带来,不方便,而且省城样式更多。
因此早就想好到了省城再装,反正来得及。
霍珝摇了摇头,“今日不忙。”
是还有些事情,但都不急,没有陪伴姑母重要。
赵慧莹只是顺带。
半个小时后,刘氏木器店的师傅来了,带来了厚厚的画册,白大太太和许弦声头对着头,看了半天,选中了一套黄花梨木的。
刘师傅问好炕屏画的尺寸,又回家拿框架、取工具,带着两个小徒弟,不到一个小时就装好了。
霍珝让人搬到自已书房,等寿辰之日再送上。
“真好!”
白大太太由衷地惊叹。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然而每次见了,都觉得自家儿媳能成一代名师。
绣得好也就不说了,还有种少见的神韵,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许弦声也觉得这炕屏画自已绣得出彩,但当着霍珝的面,觉得很不好意思,谦虚道,“母亲谬赞!”
霍珝也凝目看着,忽然道,“姑母,能不能劳烦表弟妹,也替我绣一幅?”
白大太太笑道,“人就在这里,你自已问。”
阿珝什么都好,就是太过拘礼。
不等霍珝开口,许弦声迫不及待地道,“当然可以,大表哥喜欢什么图案?”
霍珝帮了她很多,是她救命恩人,能有所回报,她求之不得。
思忖片刻,霍珝缓缓道,“白玉兰。”
她给他的感觉,就很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白玉兰,白净柔软,姿态美妙,有着清幽的香气。
许弦声笑道,“我有白玉兰的画样......”
霍珝打断她,“不,我自已画。”
许弦声现在也学会了恭维人,“大表哥还会画画?真厉害。”
霍珝:“一般。”
说完就去找画具。
白大太太抬手掩唇,打了个哈欠,笑道,“阿珝慢慢画,慧莹你在这儿等着,我乏了,得去歇会儿。”
等许弦声反应过来,书房里就只剩了她和霍珝。
春杏也不在,候在门外,因为霍珝不喜下人进书房。
霍珝的画具也找到了,在宽大的书桌上铺开宣纸,一边调颜料,一边构思图案。
他没有看许弦声,但许弦声还是局促不安,不知道是该上前围观,还是站在后面等。
很想也去门外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