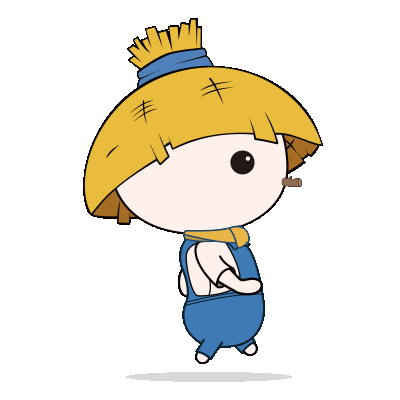许弦声为何知道得这么清楚?因为她也在场。
白老太爷特意派人叫她去的。
接下来几天,白大太太狠狠整治了议论她的下人,家下各处,也管得更为用心。
眼见婆母因自已而受老太爷的责骂,许弦声惶恐万分,连连请罪,也做好了被罚的准备。
但白大太太不打她,也不骂她,对绿萝院的供应也不曾减少。
只是不想看见她,让她没事别出来晃。
她又一次去请罪时,白大太太的丫头金桂阴阳怪气地说,这可当不起,要让老太爷知道了,又是一场事故。
另一个丫头桑叶说,三少奶奶照顾好自个儿,大家就都烧高香了。
她只得回绿萝院,轻易不敢出现在白大太太面前。
“......霍少帅手下好多兵,可威风了!”
春杏还在喋喋不休。
许弦声起身,走回卧房,打开立在东南角的大木柜。
里面是一匹匹叠放整齐的布料。
为了面上过得去,赵家给她的嫁妆不少,其中有四匹绸缎。
白家又有布庄,每个月,白大太太都会令人送来两匹花样新式的料子,让她自已裁衣穿。
“三少奶奶,你要干嘛?”
春杏跟过来。
许弦声:“裁衣。”
她后来仔细想过,为什么霍少帅的扈从,会将她当成下人?
想来想去,想到了原因,衣着打扮。
祖父祖母教养她,以朴素为主。
衣裳也是老成黯淡的颜色,靛青、黑灰、老蓝、酱紫。
她绣工很好,有次偷着在衣角绣了支梅花,被祖父训斥了一顿。
祖母也说,好女子不该妖妖娆娆,要本分老实。
慢慢的,她也习惯了。
嫁到白家之后,偶尔穿件颜色鲜艳的衣裳,就浑身不自在,仿佛变成了祖母口中妖娆轻浮的坏女子,赶紧脱下。
有些下人偷偷说她是乡下老太太。
这一世她立志要改变,那就先从衣着开始吧。
“不年不节的,裁什么衣!”
春杏嘴里嘀咕着,也帮她翻找。
并且按照她往日的习惯,找的尽是青灰黑。
许弦声拿出一匹天水碧丝绸,让春杏先在窗下的大桌子上铺一层白棉布,再将丝绸放上去。
春杏难免有些吃惊,“三少奶奶,你不是不喜欢这颜色吗?”
许弦声拿着大剪刀开始裁剪布料,淡淡道,“现在喜欢了。我今年才十六岁,正该穿些轻盈娇嫩的衣裙,不能老气横秋。”
关系还没彻底恶化时,白大太太就曾这么指点她。
后来就什么都不说了。
送来的布料,也全按她的喜好,一眼看去灰扑沉重。
“三少奶奶,你的手真巧!”
无论看多少次,春杏还是不能不赞叹。
别人裁衣,总要先量,但三少奶奶不用。
她的眼睛仿佛就是尺,精准无比。
只是,这样巧的手,尽用来做那些老太太衣裳,未免太过浪费。
好在今日选了好看的布料,约莫是醒悟了吧。
要她说,三少爷看不上三少奶奶,情有可原。
哪个正当年华的富家少爷,看得上乡下老太太似的女子。
许弦声:“从小练着,也就巧了。”
祖父祖母十分重视她的针黹女红,六岁起,祖母和柳妈就教她针线。
柳妈擅长裁衣,祖母擅长绣花。
十二岁时,还专门请了县里退下来的绣娘,教导了她两年。
足足花了五十个大洋。
家里也不是很富裕,她不想让祖父祖母破费,祖父却说,妇功头等紧要,宁愿别处省一省,也不能让她这一项比别的女子差。
这么些年练下来,不巧也难。
春杏盯着她,忽然疑惑道,“三少奶奶,你好似变了。”
她说不上来,明明还是那个人,却又感觉不太对。
许弦声头也不抬,“长大了,就该变了。”
死过一回的人,不变等着再一次枉死吗?
她还没想好怎么做,但跟上一世反着来,总是不错的。
春杏高兴起来,“变了很好!”
跟着以前呆板无趣的三少奶奶,可没什么指望。
又撺掇许弦声,“三少奶奶,你做得快,要不,也孝敬大太太一件?”
府里自有针线房,大太太的丫头仆妇里,女红好的也不少。
但儿媳妇孝敬的,始终还是不一样。
许弦声停下手,“你说得对。”
自已的衣裳也不做了,先去找布料。
她想赶在霍少帅到来前送去,时间就有点紧,做别的来不及,只能投机取巧,做套寝衣。
尺码也不用量,她记得白大太太的身形。
况且寝衣无需太贴身,尽可放宽一两寸,穿着更舒服。
选了柔软的月白缎子,飞针走线,不到下午就做好了。
让春杏立时熨好,便要送过去。
春杏趁热打铁,试探道,“三少奶奶,要不,咱换件衣裳,换个发式?”
老太太养大的,也不必非得跟老太太一模一样吧。
许弦声正有此意,当下翻箱倒柜,找了件梅染色半袖旗袍换上。
这还是嫁过来后白大太太送的,样式极为新颖,腰掐得很细,胸也比较突出。
看着西洋落地镜中娉婷婀娜的女子,许弦声本能地不安。
“不规矩!”
祖父、祖母的训诫声,仿佛在耳边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