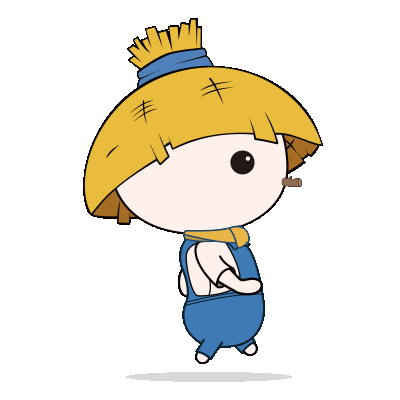堂厅两侧的绣花灯烛光明亮。
在烟雾般朦胧的光影中,宁晚棠身着品月色绣山茶花纹的裙衫,云鬟雾鬓,粉黛薄施,举手投足间清雅出尘。
她抬起头,静静朝着他这边看来。
两道视线在夏夜燥热的空气中碰在一起。
看着那张娇柔明丽的脸庞,裴知叙呼吸微窒。
“不知陛下深夜登门,是有何事?”宁晚棠施施然行了个礼。
裴知叙敛眸回神,“是有要事。”
说着,他扫了眼堂厅中的奴仆,这些人立马心领神会,躬身退出堂厅。
二人落座。
裴知叙瞧了眼坐在主位上的宁晚棠,淡声道:“朕今早没有下令重查宁家旧案,阿宁可怪朕?”
闻言,宁晚棠眉心微动,迎上他洞若观火的目光,她只能真假掺半说:“自然怪过,可后来一想,给阿父定罪的人是先帝,陛下不愿重查,我没有资格怪罪。”
“逆王逼迫宁氏,你大仇得报,辞官离京时,走的毅然决然,为何今日又想着替宁家翻案?”裴知叙问。
有些事,他必然要问个清楚。
朝中频繁提及宁元修,她又将廖权‘送’到京兆府,将真实身份暴露于人前,让他不得不把旧案提出来审查。
他想知道阿宁对他从始至终,是否只有利用。
这个问题,叫宁晚棠沉默了良久。
她缓缓起身,视线越过敞开的门窗,落到院中盛开的海棠花树上。
“十五岁,我抱着替宁家翻案的决心入京,甚至在私下暗查,想找到阿父被诬陷的证据。可越查,我的心越凉。”
她双眸平静望着庭院:“宁家只搜出白银五万两,不及前朝一个被判斩首示众的六品小贪官的十分之一!那时我才明白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是阿父贪污渎职,而是先帝憎恶阿父。只要先帝在位一日,宁家的冤情便永远无法昭雪。”
裴知叙久久地沉默了。
再开口时,声音带了一丝苦涩,“那朕登基时,你为何不告诉朕?”
宁晚棠神色如常:“陛下还记得京都是怎么说我的吗?贪慕权势、不择手段、心肠恶毒,陛下刚登基,就连授我官职,都受到重重阻挠,更别说替宁家翻案了。”
原来如此。
裴知叙的声音哑在了喉咙里。
当年初登基,他顾忌良多,手段不够强势,总想着让阿宁等等,再等等,慢慢磨那些老臣,他们早晚会同意,却忽略了阿宁的心情。
“陛下方才问我为何想要翻案。”那双乌眸似有水光闪动,“今早朝会上,只说了大哥割舍换粮,陛下可想知道我阿母怎么死的?”
裴知叙眉头紧皱,静静等她说下去。
“大哥年少中状元,是阿母最重视,最引以为傲的儿子。阿母知道大哥割舍换粮之后,病情愈发严重,不愿拖着病躯拖累我们,半夜吊死在院中的海棠花树下。”
回京时,本没有想过要翻案,可看着满院盛开的海棠花树,她心底的仇恨便越来越浓,这些海棠花每时每刻都在提醒她阿母的死。
裴知叙的唇线逐渐绷紧,望着她背影的眼神满是心疼和懊恼。
话尽于此,宁晚棠缓缓转身面对裴知叙,一双清凌乌眸在夜色里格外淡漠,“陛下还有想问的么?”
堂厅内沉寂一阵。
裴知叙喉间像是扎了根刺,眼底也略过一抹晦色。
良久的无言,让宁晚棠的心慢慢沉下去。
胸间的诸般情绪并未因一时的宣泄而平静,反而惊涛骇浪般不断翻涌着。
她抬步走向裴知叙,在他惊愕的目光中,吻上了他的唇。
…
明月高照,夜风徐徐,正是万籁俱寂时。
元佑独坐在镇抚司议事堂内,身上并未穿官袍,只着一件普通的墨青色常服。
视线垂落在佩刀横放在面前的桌案上,神色冷峻,若有所思。
角落里的铜壶滴漏己走到亥时三刻。镇抚司无比寂静,只偶尔传来几声啾啾虫鸣。
轻微的嘀嗒水声落在元佑耳朵里,好似被无限放大,不断拉扯着他的情绪,清阔眉宇间带着一种难以揣测的深思。
良久,似下定了决心,他拿起桌案上的佩刀,大步往议事堂外走。
刚走到二堂门,就见院落中站着八名穿着深色劲装的锦衣卫,这些人都曾追随过宁晚棠,也都知道了金銮殿上发生的事。
两方对视,没有多说一句话,便己知晓彼此在想什么。
承景帝若不重查旧案,宁晚棠就要流放岭南。曾经的旧部或是平步青云,或是娶妻生子,即便有心救人,也有不少的顾虑。
最后剩这八个人聚在这里,只等元佑一声令下,闯进宁宅救人。
元佑那双上扬的凤眼深沉地盯着他们,压低嗓音道:“可都想清楚了?违抗圣令,是要杀头的。”
“元大人不是己经决定了么?”
“我们誓与元大人共进退。”
元佑虚目,抬步迈下石阶,嗓音冷冽:“走吧,让殿前司那帮人看看,镇抚司想救人,他们拦不拦得住。”
…
宁宅。
庭院风吹树影摇。
裴知叙睁大眼睛,愣愣看着近在咫尺的娇颜,两只手无措地悬在半空。
不同于风月之事的酣畅极乐,这个吻,叫他如坠云端,晕晕乎乎。
察觉到面前之人身体僵硬,宁晚棠慢悠悠睁眼,退开半步,于影绰晃动的烛光中道:“陛下不喜欢?”
神女在怀,裴知叙如何能拒绝得了。虽不知阿宁为何突然这般热情,但她愿与他亲近,他自是求之不得。
他勾住宁晚棠的腰,缓缓凑近那抹鲜花瓣儿似的唇。心底掀起的情绪过于澎湃,让他几乎有种难以承受的预感。
两条手臂渐渐勾缠上裴知叙的脖颈,宁晚棠红唇微张,毫无保留地由他吻着。
堂厅的门尚且大开着,庭院幽深,青檐黛瓦,随时都可能会有奴仆路过。二人却无暇顾及,裴知叙看着怀中的人,那双深邃的眼睛几乎要将她整个溺于其中。